茧衣,原名葛璐璐, 80后,诗歌写作者,现从事媒体工作。代表作《拈花者》、《打牌》、《孔家少爷》、《放荡词》等,曾在《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多种刊物及多种流派选本发表大量作品。
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同时也是诗人。她们以柔软细腻的诗心,勾勒着生活点滴、倾诉着爱恨情仇。她们用人生来膜拜诗歌,也用诗歌温暖人生。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中国诗歌网最新推出“女诗人系列”访谈,带你近距离欣赏那一道道亮丽风景。欲知“女诗人养成记”,请随我们一起,探访她们的生活现场,感受她们文字中的温度。

“大荒唐接近真情”,此话出自茧衣的诗《放荡词》,是一个心气高蹈的女诗人无限情怀的写照。茧衣诗歌的最大特征是叙述戏剧化,就像布莱希特论戏剧时说的那样,她善于在叙述的“横断面”上停留、放大,制造陌生化效果。此外,茧衣善于白描,透过平淡直接、去皮露骨的叙述,可看出诗人心气与语言性情的合一。
茧衣的很多诗,充满戏剧化叙述,貌似讲故事。与布莱希特所期望的戏剧一样,茧衣的诗不刻意把读者卷入叙述事件,不在于吸引读者关注叙述指向的结局,而是吸引读者关注叙述的“进行”。茧衣的诗,强调人的动机大于强调人的本能,叙述中的人物充满未知。通过这样的叙述,诗,就为读者的客观判断力提供了较大空间。有了“读者客观判断力”这个空间,叙述过程能否保持读者的感受已是小事一桩,重要的是,诗已经能让读者把感受变为认知,促使读者做出抉择,唤起他们的行动意志。
茧衣的诗,善于白描,语言随缘自在,从头至尾没有预设的“阴谋”,只有平静的叙述中暗藏的可能的突变,是一种去皮露骨的直接抒写。何谓去皮露骨的叙述?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评价陶渊明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一语天然,豪华落尽,即是去皮露骨、直接抒写的叙述心法。
——白鸦 :评茧衣诗歌:大荒唐接近真情
浪漫、孤独、旁观、自我满足、不急不慌,任你风卷云舒,我自拈花微笑。这是一位对生活充满了理解和温情的人,知道生活的美好,也知道它的疼痛,因而小心翼翼,从不触碰那些“疼”的部位,情愿让那些构成了疼痛的伤痕结痂愈合。
应当说,茧衣的诗并不是我一向心仪的那一类写作。安琪在谈到她从骨子里所偏爱的诗歌语言和写作类型时说:“第一,它的语言必是锐利的、强悍的、裂变的、先锋的、带血的……一句话,它不是美的抒情的光滑的,也不是口水的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的。第二,它肯定为汉语诗歌提供了新的叙述方式或写作角度。一句话,它肯定不是平庸写作!”安琪说得很好,毫无疑问,我一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写作,但这并不妨碍我私下对茧衣一类写作的某种惊讶和兴奋。在茧衣的诗歌里只有温和的经验,找不到激烈的批判,生活的真理以缓慢的节奏呈现。我们甚至可以说,茧衣的诗是很“小资”的,有温文尔雅的情调,有从容冷静、不急不火的优雅,却没有刻骨的力度。这样的诗歌让我想到花的存在——花是无力的,通常生活在另一世界,孤绝而冷傲,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但当春天来到大地,成千上万的花朵却以自己的美丽改变了世界。它们并不干预世界,只是悄悄地、坚定地加入进来,以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美的法则呈现——茧衣当然不是花朵,她只是一位拈花者,极端自爱而且自信,透过茧衣式的冷静,我们一样看到某些生活的真相。这说明诗歌原本十分宽阔:既可以是直奔心灵的精神急流,也可以雍容平和,或者仅仅只是花朵一样的存在,或仅仅只是某种拈花的姿态——面对世界,茧衣式拈花微笑的优雅和从容,也是诗美的一种。
茧衣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故事,故事是粗线条的,通常携带着某种神奇的能量,一路大步流星,将阅读的惯性打破,更多地与心灵相关;注重细节刻画,却不以细腻见长,只呈现那些关键的部位,恰如中国书法里“铁划银钩”的境界,非常值得期待。
——刘诚:评茧衣 《任尔风舒云卷,我自拈花微笑》
诗写人,但如何依靠诗性的语言把人的骨肉和灵魂统一,雕琢出一个内心波澜而文人气象生动的人,却非人人都能驾驭。它考验诗人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境界。
诗人选取的情感物象是:“一支湖笔/两个眉目清秀的女人”。由此奠定了孔家少爷的人生脉象。一支湖笔暗示着诗、书、画,转喻在文治,是对太平盛世的期待。两个女人则是儿女情长的人间性情。“他日子过得很好/在酒馆的墙上题诗/换半壶烧酒/和老板娘调情/讨两份胭脂”,以白描笔法,书写出散淡、率真、旷逸。
男儿须眉,他不关心政治和八股和清兵入关的时候出走的关系是国破家亡的仇恨。孔家少爷有责任,有大是大非面前的担当,有高尚的节操。“他只是骗吃骗喝”属小节、放浪。“偶尔画几根竹子,和竹子旁边的鸟”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名仕风流的显现。诗从文人安享到国难当头的奋起作为,传神一个翩翩公子,“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属于他人”的家国情怀。诗在巨大的反差和转折中看见结构的力度。
——王之峰:一支湖笔——评茧衣《孔家少爷》
1、花语:你的诗以叙述见长,叙述对你的诗歌是否有特殊意义?
茧衣:并不是非常刻意的在写叙述诗,可以说叙述是非自觉性的。开始写诗是一种表达的需要,一种着迷于想入非非的结果。喜欢发呆,喜欢想象画面和情节,这是从小养成的睡前娱乐。比起眼前的事物,背后延展的人物和人生更能吸引我,比如在南方的古宅游荡时,感觉每一节旧楼梯,每一扇窗都是一个未打开的剧本,想象背后曾经晃动的人影和他们交织的人生,对我来说是一件挺享受的事,所以后来就写了《古宅旧事》,但当时我并不确认那算不算诗。
我的想象不成体系,碎片化,所以诗是更容易承载这种发散式想象的形式。有时我觉得写诗可能是一种偷懒的表达方式,不是说懒得写太多字,而是怕字写多了自己就露馅了——急于述说所想,但又不想或者说不能把握小说那么精深的结构。
更妙的是诗歌的叙述可以变形,可以很主观,在变形的叙述中加入自己的情感和情绪,这和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有关系,一直比较抗拒直接、外露的情感表达,所以在叙述与自己不想干的情景时偷偷嵌入自己的情绪让我有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我更喜欢冷静、旁观式的叙述,但其实每一个叙述,我都把自己隐藏在里面,每一个他其实都是我。
有时,不再用第三人称,“他”恢复了“我”的本来面目,这可能与对自己的认知改变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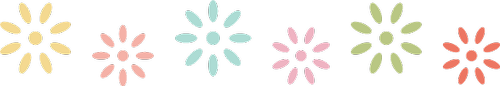
2、花语: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以前的北京有霾吗?面对如今隔三差五的十面霾伏,你有想说的话吗?
茧衣:我对环境问题一直感觉比较迟钝,没有北京咳,分不清雾和霾,一度觉得总提这事的人有点娇情。后来随着环境越来越恶化才觉得这可能真是个问题,因为怀孕和生小孩,为孩子稍微注意了一些,前一阵才刚刚买了空气净化器,大概也是心理安慰吧。
说不好北京以前有没有霾,但沙尘暴肯定是有的。北京孩子童年的记忆里一定有妈妈的红纱巾,每当北京刮大风和沙尘暴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蒙在头上,纱巾是透明的,上面有一些金银丝,透过它看街上的路灯,光线会有一种奇妙的变形。
对于柴静这样的斗士我是佩服的,但自己做不来。我觉得斗士可能更需要一种愤怒的情绪,但我对愤怒还是比较陌生,对一些社会事件我的反应往往是怜悯多于愤怒。
其实不光是对环境问题不太敏感,我对外界发生的事一向比较后知后觉,可能是因为更关注内心吧。忘了是谁说我有一种钝感力,我对这个说法还挺喜欢的,也蛮准确,钝感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
3、花语:最早写诗始于何年,诗歌写作经历过哪些阶段?
茧衣:说不好写诗始于何年。中学阶段比较自卑,发现文字可以让自己舒适一些。写的东西个人认为可以叫做诗的,进入这阶段大概是上大学以后,零星读了一些现代诗,在网上接触到了网络诗歌,找到了自己在审美上比较认同的一种文字,慢慢也找到了一些语感。后来的一个飞跃阶段应该是2005年左右在当时的诗论坛上面认识了白鸦、你等一些朋友,慢慢得到了更多认可,我这个人可能很需要认可,内心充盈的时候才能有一个进步。
曾经有人说我到25岁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写什么东西了,当时不服气,特意在25岁生日时写了一首诗。但预言往往有一个时间的误差,果然我到28岁以后就不大写东西了。可能与结婚过上普通女人的家庭生活有关系,也可能和工作上的变动有关。之前在工作上一直兜兜转转,不令自己满意,远离文字的工作让我更想亲近文字。后来找到一份做新闻编辑的工作,热情就转移了,但慢慢发现自己反而对文字产生了一种疲劳感,不再有初恋般的兴奋。
听很多写诗的人描述过一种状态,类似于“谁执我笔写文章的感觉”,这无论如何应该算是一种天赋,是上天给这个人的一件礼物。但礼物可能也分大小,我的小礼物用尽后,大概只能靠经验写作了,但很不幸,我并没有积攒太多经验,所以现在应该是一种“待苏醒”状态,但在情绪波动时仍然寄望于文字的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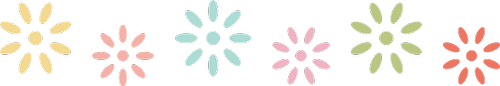
4、花语:你对好诗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茧衣:应该没有一个标准。诗歌本来就是内心很个人化的东西,比如某一个句子打到我的内心了,或者从审美的维度上让我醉了一下,于我这就是好诗。但没有打到我内心的,并不一定不是好诗,可能只是与我的生活体验距离比较远罢了。
我认为诗的价值就在于与外界从审美到内心交融的一瞬间产生的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一首诗的诞生,于万千人中,只要产生过一次这种化学反应,应该说这首诗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贯以好诗与否的概念,只能说诗是否具有价值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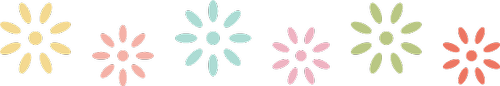
5、花语:除了诗歌,你还喜欢哪些艺术门类?有崇拜的偶像吗?
茧衣:艺术感受力应该也是一种天赋,区别于艺术鉴赏能力,鉴赏是一种经验,但感受绝对是天赋。和诗歌一样,能打到我的就是我喜欢的。比如印象最深刻的是被莫迪里阿尼的画打到。昆曲也是比较能令我沉醉的一门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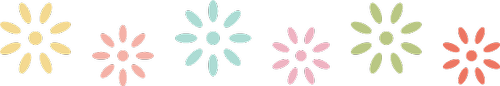
6、花语:诗人周公度说:说谎乃万恶之源,你是否认同?
茧衣:对此感受不深。骗子大概也分天赋型的和经验型的,有人天生就会察颜观色,对人心有一种敏锐感,而且心理素质好,不会轻易地紧张,如果这种人把他的天赋用于行骗,他一定是天赋型的骗子。
谎言的初衷不同其性质也自然不同。用于行骗谋利的当然是可恶的。善意的谎言也有,这个无法做出评价,只能视其结果而定。也有一种谎言最终是欺骗和麻木自己的,这种也说不上是可怜还是幸福,醉在谎言中的一生也是一生,外人无法评断。

7、花语:口语诗与口水诗的区别在哪,请荐读一首特别漂亮的口语诗?
茧衣:区别应该在于语言的质感和内心的丰盈吧。漂亮的口语诗很多。有些当时拍案叫绝的,记得阿坚有一首叫《大垃圾山》的,但很遗憾,找不到原诗了。于坚的《垃圾袋》也挺喜欢。
在此节选后面的一部分吧:一直按照最优秀的方案生产它/质量监督车间层层把关 却没有/统统成为性能合格的袋子/至少有一个孽种 成功地/越狱变成工程师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轻它不是天使/我也不能叫它羽毛但它确实有/轻若鸿毛的功夫/瞧/还没有落到地面透明耀眼的/小妖精 又装满了好风飞起来了/比那些被孩子们渴望着天天向上的心/牢牢拴住的风筝还要高些/甚至比自己会飞的生灵们/还待得长久因为被设计成/不会死的只要风力一合适/它就直上青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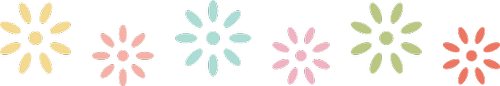
8、花语:对父母你足够孝顺吗?在你看来何为孝?
茧衣:这个说不好。我这个人比较容易活在自己的内心,有时会忽略周围人的感受,对此我也常常内疚。至于何为孝顺,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父母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比如家庭困难的,物质就是孝顺,很少回家的儿女,陪伴就是孝顺,但如果你和父母生活,起居由父母照顾,那么陪伴就说不上是一种孝顺了。最好的孝顺肯定是心灵的慰藉,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父母的一些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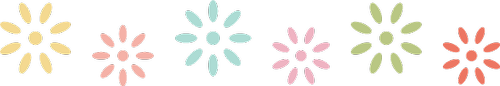
9、花语:请说两句影响过你的,特别牛B的人生格言!
茧衣:这个暂时没想到。歌词算吗?有一句我听错的歌词:“我敬你一杯自在,不要回敬我感慨”。我觉得挺好,挺喜欢哼的。前两天才知道,原歌词是:“我敬你一份真爱,不要回敬我感慨。”是不是感觉比我听错的版本要low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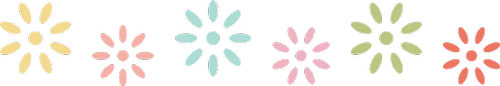
10、花语:喜欢哪些运动,最常用的健身方式有哪些?
茧衣:以前会去后海划龙舟,但说实话,加入这个龙舟组织最早是出于社交的目的,运动倒在其次。上学时的我非常封闭,朋友不多,社交能力不强,还有点自卑,父母为了鼓励我多社交带我去后海加入了龙舟队。有很多老外在里面,加入这个组织顺便也能练练英语,我猜这个组织里的很多中国人加入的初衷也大多是社交或者练英语。不过,龙舟是个很好的运动,需要集体配合。

11、花语:你以貌取人吗?相为心生,这句话有道理吗?
茧衣:肯定是属于以貌取人的。但貌不一定是颜值,有时是一种气场,应该是内心散发出的一种东西,大概就是你说的相由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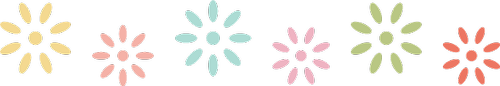
12、花语:相信属相和星座吗?你是双鱼座,你觉得这个星座是否有缺陷?
茧衣:说不上相信不相信,但一切带有宿命论的说法都让我着迷。沉迷于自我的世界,不一定是双鱼座的缺陷,但肯定是我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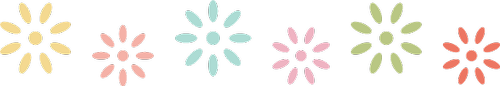
13、花语:假如现在的你,在北京的某个街道遇到了十八岁的你,你会对她说点什么?
茧衣:可能会提醒她早点用防晒霜吧,现在越来越黑了。
14、花语:你旅游过的地方,最喜欢哪儿?你心目中诗意的城市是哪里?
茧衣:应该是重庆吧。是一种带有宿命感的喜欢,去了就喜欢了,虽然只去过一次。说不上来因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那里一种奇怪的植物,或者是那些歪斜的小街,但我希望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宿命,可能和前世有关,轮回之说对于我来说也有一种到致命的诱惑力。坐在江边,眼前就有很多人影晃动,他们的人生交织着我不曾去过却很想触及的时代。今生以前我是谁,今生以后谁是我,我又将和他们之中哪一个有所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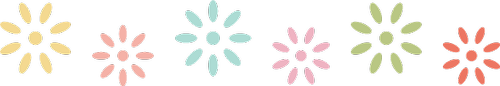
15、花语:你喜欢的中国诗人有哪些?
茧衣:启蒙时候最喜欢台湾的洛夫,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审美的吸引。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那个阶段喜欢的就是这种语感。
在接触网络文学以后,在榕树下看到一个叫叶想的浙江诗人的诗。非常喜欢,到现在也喜欢他的东西。不是很激烈的那种文字,有美感,有节奏感,也有说不出来的心灵相犀的东西。有一句当时非常打动我,具体的记不太清楚了,在网上也找不到了,大概意思是说,对不起,陌生人,我错过了本该与你相爱的一生。是那种最能触动我的宿命的遗憾。
开始喜欢的都是很具形式美感的句子,像洛夫的那种。慢慢地可以欣赏一些内心沉静的诗句。比如江苏诗人鸣钟的《两只小兽》:“橱窗!你不要透露/在你清洁无尘的面孔上/张望着的,卑贱的小老鼠/它看见了,另外一只同样卑贱的小兽/像个小绅士,拖着外套似的影子/你也不要透露——/阳光下,那些美好的食物/有着在暗夜里看不到的错误和暴力/让两只小兽安全地经过/不要留下一点点对于美好的恐惧。”这是诗的后两段,非常打动我的文字,有一种善良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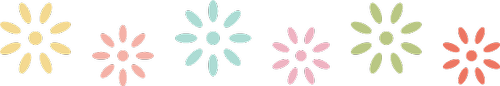
16、花语:你是逆反心特别重的人吗?逆反心是否也成就了你的今天?
茧衣:谈不上成就。逆反心理应该是青少年时期有的吧,我的成熟度低,青春期也比较晚,所以大概20几岁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逆反心理。但如果到现在还些逆反,可能就是青春期后遗症吧,但肯定不会表现得特别强烈,毕竟已为人母。当然逆反心理对于文字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活力,成熟度越高,这种活力肯定会磨损得越多,这时候一些沉静的东西就会浮上来,成为人的主色,这是自然规律。也有一些诗人一直保持活力,他们大概是真正的天才吧。
但从另外一个维度讲,逆向思维是有的,这应该是一个写诗的人的标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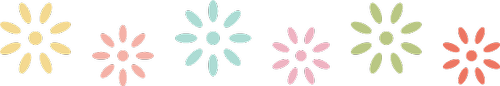
17、花语:你经常和女诗人赵妙晴在一起,为什么?
茧衣:气场相合。和妙晴相识也算以文会友,首先是被她的文字感染了。看到她的第一篇文章印象很深,叫《一生》,写一个老妇人临终的一刻,叫一生却只写一刻,好像一个水滴里有一个世界。我为此还写了一首短诗,“一生隐于水/被梨花看在眼里/于是落下/于是又归于寂寞”。和那篇文字相比,这个不能叫诗,只是一小段读后感。还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孩子被一束光吸引,那种细腻的刻画,让人无法相信文字还有如此魔力。
气场相合的人隔很远也能闻出彼此的气味,看文字就知道是相投的人,所以见面都不用寒暄,好像彼此已经认识很久。
妙晴说话很有趣,不是那种故意的有趣,是一种旁观的冷静的有趣。总觉得她骨子里有一种淡淡的倔强,不会直接对抗什么,她只是静静的伸出手,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拒绝的姿态,也可以说她只是和谁打了招呼。
她的有趣还缘于刚才说的那种逆向思维,一种绕到后面去看看的欲望,一种随时可以转身的从容。当然她也是专注的,对于她恪守的审美,或者对于一些别人会忽略的美,她有一种极致的专注,比如,曾经吸引过我的那束光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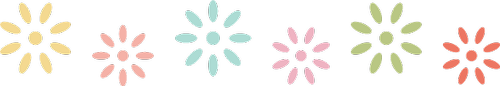
18、花语:真诚是一种能力,“真诚”对一个诗人重要吗?
茧衣:当然重要,掺了杂念的文字不会打人,这就是最重要的区别。
{Content}
 (2次)
(2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8次)
(8次) (2次)
(2次) (2次)
(2次) (2次)
(2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4次)
(4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2次)
(12次) (4次)
(4次) (2次)
(2次) (2次)
(2次) (3次)
(3次) (1次)
(1次) (6次)
(6次) (6次)
(6次) (3次)
(3次) (1次)
(1次)除每日好诗、每日精选、诗歌周刊等栏目推送作品根据特别约定外,本站会员主动发布和展示的“原创作品/文章”著作权归著作权人所有
如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用于他处和/或作为他用,著作权人及本站将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诗意春秋(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京ICP备19029304号-1 京ICP备16056634号-1 京ICP备16056634号-2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Copyright © 2006-2015 全景统计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