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陈树照诗歌阅读印象
爱的领受者与吟唱者
——陈树照诗歌阅读印象
文/辛泊平
关于诗歌,我们有太多的阐释版本,谁也无法最终统一诗歌的定义。许多时候,诗人们就像孤独的牧羊人一样,在自己理解的草场上放牧着自己的情愫和灵魂,书写着自己认可的诗行。这几乎也是新时期以来,网络论坛上关于诗歌争论的主要原因,谁都觉得是自己而非对方掌握了诗歌的命名权。当然,不可否认,一些诗人为了趋同的诗学策略,打出同一面旗号,刻意地书写审美情趣、艺术技巧相似的诗歌文本,形成所谓的圈子写作或同仁写作。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关注的似乎并不是热闹的、口号一样的诗学宣言,而是某位诗人的具体作品。所以,我一直对所谓的流派持警惕态度。比如莽汉派,李亚伟就是李亚伟,万夏就是万夏,他们谁也不代表谁;比如文学史上的第三代,于坚和海子肯定不是一回事,韩东和西川也绝对不能互相取代。和流派有点相似的便是诗人地域性的描述和整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文字,言说者旁征博引,言之确凿。但就是无法真正打动我。我承认,一个地方的诗人肯定有相似的文化背景,那些风土人情也会形成一种文字性格。然而,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这些曾经非常重要的分析参数也变得格外模糊。在生存困境、灵魂求索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挽留等方面的趋同性几乎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这是现代语境下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所以,在许多时候,当我面对某一地域的诗人之时,我不会为了方便,用先前的某种地域印象肢解诸多个体,而是更愿意笨拙一点,谨慎一点,面对一个个独立的文本,从那里触及和感受鲜活而独特的诗歌灵魂。比如陈树照,这位生于中原大地,而又工作生活在北方边陲的诗人,我们很难用单一的地域性描述概括他的诗歌。因为,他的作品并没有仅仅在一个向度上挖掘,而是无限敞开,用属于诗歌的抒情,表达着他对世界与人生的咏叹与赞美。
是的,就是咏叹与赞美。在当下,这种情怀也许显得陈旧与落伍,因为,人们更习惯那种电视与网络的花絮,习惯了流行杂志的小资,习惯了地方小报的噱头,习惯了那种无聊的调侃和包袱,而淡忘了人类正常的感情和优雅的表达。而陈树照却在这样娱乐无限扩张的文化背景下,坚守着人类正常情感的诗意表达。这是诗人的生命自觉,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在对陈树照持续的阅读中,我感受到了诗人心中浓浓的爱意,那种爱不仅仅是故乡之情,血缘之脉,更是广阔的大地与天空,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旅,是无法分割的时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是一种有历练的爱,是经过了苦难洗礼与灵魂救赎的爱。所以,它真实而自然,如汤汤的河水,一贯如一。他笔下的家乡,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表层描摹,而是一个个血肉鲜明的亲人和乡亲。他写父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 “他怕我和弟弟娶不上媳妇/哥哥 姐姐住不上新房子/母亲的老寒腿过不了冬/这些他都怕 怕得失眠 怕之入骨/怕病虫害 怕无米下锅”(《父亲活着》)的乡下老人,他们什么都怕,那不是他们怯懦,而是他们经历过什么都可以毁灭一个人生命和尊严的时代和梦魇。所以,他们的怕就是生存的经验,是对下一代人的惦念和牵挂。他写母亲,“拢扎苍白的头发/挽紧灰色的裤管 左手按住衣服/右手举起棒槌 一下二下/重重砸下去 那声音 /和我手中使唤老黄牛的叫声/很接近 沉闷中总是带着苍茫”(《洗衣的母亲》),这样的母亲是具体可感的,她不是模糊的印象,而是不停操劳的母亲,是让人心疼的母亲。他写乡下田埂上小憩的女人:“搓去手上的泥 咕嘟咕嘟/喝空罐里的水 一手擦脸/一手抱起哭喊的孩子 靠树根坐下/露出那双白颤颤的奶子”,这不是什么装饰画,而是真实的生活场景,细腻而又扎人。他写生病之时的大嫂,写她在飞机上、医院中,写她死后大哥与“我”的反应与感受,写得肝肠寸断。这是因为,陈树照的诗歌写作撕开了那些影视关于农村的美好设想,让读者近距离感受火热而又悲伤的生存核心。这样的写作是有良知的写作,面对普遍的乡村状况,诗人没有美化,也没有刻意放大它的苦难,而是忠实于自己的视觉,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把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呈现出来。我喜欢陈树照这些写亲情的诗篇,因为,它忠实于生存的现状,没有掩饰,也没有拔高,而是贴心贴肺,真实可感。
在对故乡的关照中,陈树照没有居高临下地俯视,更没有矫情地放大伤口,而是恰如其分地融入其中,以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双重视角打量曾经养育自己的家乡——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赤脚走路
走南冲的沙土路 北岗的荆丛路
西坡的青石路 东畈的泥泞路
要学会赤脚下冰渣的稻田
穗芒如刺的麦地 豆地 高粱地
要钻红麻林 槐树林 枣树林 甘蔗林
爬陈梨山 左桃山 牛角山 高墙矮墙
要学会赤脚挑担走几十里山路赶集
腰不酸 脚不痛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赤脚积肥
掏粪坑 灶坑 污水坑 臭水坑
要习惯人粪 牛羊粪 猪马粪
鸡鸭粪 猫狗粪散发的各种气味
要耐得住苍蝇 牛虻 蚊子 小咬
蟑螂 老鼠 虱子 虮子 蝗虫的袭击
要学会亲近萝卜 白菜 黄瓜 土豆
珍惜每一粒米 每一把柴 每一根线
不吝啬每一滴汗水 心肠要软
腰身要硬 为人要厚道 手掌要有力
比如套牛犁田 耪地撒籽 浇水施肥
除草除虫 收割打场 脱谷扬糠……
这些都要会 车轻驾熟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享受
躺在地头睡觉的幸福 要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编竹筐竹篓 编草鞋笤条 织毛衣
男人 会修椅子锄头 磨镰炝刀
雨天用油毡纸砖头压实屋顶
女人 会烧饭洗衣 做针线 奶孩子 洗尿布
要喝井水 田沟水 吃糠麸 吃树皮
吃生瓜野果 野菜胃不疼
照样有力气 要习惯黑暗里走路
再黑的夜晚也能摸回家
死也要埋在自己的土地里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光着膀子
种庄稼 给家禽看病 给小羊 小牛接生
给猪狗 牛马配种 要习惯冬夜一家人
围坐火盆 灯下缝洗 积咸菜 说家常话儿
想打工在外地的亲人 不怕狼嚎 狗叫
要有飞蛾扑火的精神 习惯土坷
石头硌破脚底 手被庄稼勒出血道道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杀鸡 宰羊 剥皮
埋人 推碾子 拉磨 能忍受歉收荒年
没米下锅 衣衫单薄的煎熬 要会掰着手指过日子
要孝道 乐善好施 红白喜事要风光着办
要遵守村规家风 要会打肿脸装胖子 不能选择出身
不能屈服命运 要有一副老茧的肩头
忍住那些没钱治病的泪水……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不低头 不埋怨
跪祠堂 跪娘亲 跪苍天
誓与土地共存亡 对一块土地
要有100%的信心与耐力 爷爷种60年
父亲种60年 你也要种60年
今天种 明天种 后天再种
种一百遍 一千遍 一万遍
人死地不闲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这是一首超容量的作品,在看似琐碎的絮叨里,其实是对中国农民命运及其文化心理的一次挖掘与梳理。苦难中的隐忍,隐忍中的守护,守护中的悲悯,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命运结构图,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提纲。那些在苦难中隐忍的农人,他们或许不知道什么是意义,但他们以自己脆弱而又坚实的肩膀,撑起了一个种族的繁衍,并使之生生不息。他们耕作,他们收获,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他们虚荣,他们忍气吞声,他们敬天敬地,然而,无论怎样,他们都没有屈服,而是像牲口一样,没有埋怨,也没有僭越,只是倔强地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者五谷,也耕耘着自己的人生。这是一首让人震撼的诗,它以集装箱一样密集的意象和情感,向我们展示了广大农村日常生活的波浪,以及更为隐秘但绝非虚构的心理潜流。
可以这样说,陈树照的诗歌从家乡出发,然后慢慢辐射,抵达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一种有根的写作。它扎根于承担了太多的泥土,并忠实于生长的规律,把生命瞬间的战栗、疼痛与幸福吟唱出来,给那片土地,也给自己的心灵。在我的阅读中,除去那些充满细节的家乡风物,他对现在生活的那片土地同样怀着深情。他写大雪,写得轻盈而多情,写雪中的人们,写得烟火气十足。所谓的故乡之外的“异乡”以及那种疏离的异乡情结,在陈树照的作品中是没有的。在他的情感版图上,没有地域的界限,也没有气候的划分,所有的价值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辽阔的感动与深沉的感恩。他是大地的赤子,是大爱的领受者与吟唱者,合着自己的节拍。
读他的作品,我经常会想起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或许可以这样说,陈树照的写作就是灵魂写作。因为,在当下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泥土的吟唱是低声的,它不可能超过那些娱乐至死的选秀,不可能超过那些真假难辨的花边新闻,它的听众不是大众,而是有沉重过去和当下关怀的少数人。所以,陈树照不在乎听者,只在乎自己的声音是否真诚,是否纯净。也正因如此,他的情感才有了更为细腻的和声,他的关怀才有了更为柔软的声部。
2012-4-28
作者简历:
辛泊平: 70年代生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星星》《雨花》《青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近百家报刊发表作品若干,并入选多种选本.作品被《读者》《中华文摘》(香港)等二十多家报刊及人民网、新华网转载,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现居秦皇岛市.
——陈树照诗歌阅读印象
文/辛泊平
关于诗歌,我们有太多的阐释版本,谁也无法最终统一诗歌的定义。许多时候,诗人们就像孤独的牧羊人一样,在自己理解的草场上放牧着自己的情愫和灵魂,书写着自己认可的诗行。这几乎也是新时期以来,网络论坛上关于诗歌争论的主要原因,谁都觉得是自己而非对方掌握了诗歌的命名权。当然,不可否认,一些诗人为了趋同的诗学策略,打出同一面旗号,刻意地书写审美情趣、艺术技巧相似的诗歌文本,形成所谓的圈子写作或同仁写作。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关注的似乎并不是热闹的、口号一样的诗学宣言,而是某位诗人的具体作品。所以,我一直对所谓的流派持警惕态度。比如莽汉派,李亚伟就是李亚伟,万夏就是万夏,他们谁也不代表谁;比如文学史上的第三代,于坚和海子肯定不是一回事,韩东和西川也绝对不能互相取代。和流派有点相似的便是诗人地域性的描述和整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文字,言说者旁征博引,言之确凿。但就是无法真正打动我。我承认,一个地方的诗人肯定有相似的文化背景,那些风土人情也会形成一种文字性格。然而,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这些曾经非常重要的分析参数也变得格外模糊。在生存困境、灵魂求索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挽留等方面的趋同性几乎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这是现代语境下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所以,在许多时候,当我面对某一地域的诗人之时,我不会为了方便,用先前的某种地域印象肢解诸多个体,而是更愿意笨拙一点,谨慎一点,面对一个个独立的文本,从那里触及和感受鲜活而独特的诗歌灵魂。比如陈树照,这位生于中原大地,而又工作生活在北方边陲的诗人,我们很难用单一的地域性描述概括他的诗歌。因为,他的作品并没有仅仅在一个向度上挖掘,而是无限敞开,用属于诗歌的抒情,表达着他对世界与人生的咏叹与赞美。
是的,就是咏叹与赞美。在当下,这种情怀也许显得陈旧与落伍,因为,人们更习惯那种电视与网络的花絮,习惯了流行杂志的小资,习惯了地方小报的噱头,习惯了那种无聊的调侃和包袱,而淡忘了人类正常的感情和优雅的表达。而陈树照却在这样娱乐无限扩张的文化背景下,坚守着人类正常情感的诗意表达。这是诗人的生命自觉,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在对陈树照持续的阅读中,我感受到了诗人心中浓浓的爱意,那种爱不仅仅是故乡之情,血缘之脉,更是广阔的大地与天空,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旅,是无法分割的时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是一种有历练的爱,是经过了苦难洗礼与灵魂救赎的爱。所以,它真实而自然,如汤汤的河水,一贯如一。他笔下的家乡,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表层描摹,而是一个个血肉鲜明的亲人和乡亲。他写父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 “他怕我和弟弟娶不上媳妇/哥哥 姐姐住不上新房子/母亲的老寒腿过不了冬/这些他都怕 怕得失眠 怕之入骨/怕病虫害 怕无米下锅”(《父亲活着》)的乡下老人,他们什么都怕,那不是他们怯懦,而是他们经历过什么都可以毁灭一个人生命和尊严的时代和梦魇。所以,他们的怕就是生存的经验,是对下一代人的惦念和牵挂。他写母亲,“拢扎苍白的头发/挽紧灰色的裤管 左手按住衣服/右手举起棒槌 一下二下/重重砸下去 那声音 /和我手中使唤老黄牛的叫声/很接近 沉闷中总是带着苍茫”(《洗衣的母亲》),这样的母亲是具体可感的,她不是模糊的印象,而是不停操劳的母亲,是让人心疼的母亲。他写乡下田埂上小憩的女人:“搓去手上的泥 咕嘟咕嘟/喝空罐里的水 一手擦脸/一手抱起哭喊的孩子 靠树根坐下/露出那双白颤颤的奶子”,这不是什么装饰画,而是真实的生活场景,细腻而又扎人。他写生病之时的大嫂,写她在飞机上、医院中,写她死后大哥与“我”的反应与感受,写得肝肠寸断。这是因为,陈树照的诗歌写作撕开了那些影视关于农村的美好设想,让读者近距离感受火热而又悲伤的生存核心。这样的写作是有良知的写作,面对普遍的乡村状况,诗人没有美化,也没有刻意放大它的苦难,而是忠实于自己的视觉,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把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呈现出来。我喜欢陈树照这些写亲情的诗篇,因为,它忠实于生存的现状,没有掩饰,也没有拔高,而是贴心贴肺,真实可感。
在对故乡的关照中,陈树照没有居高临下地俯视,更没有矫情地放大伤口,而是恰如其分地融入其中,以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双重视角打量曾经养育自己的家乡——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赤脚走路
走南冲的沙土路 北岗的荆丛路
西坡的青石路 东畈的泥泞路
要学会赤脚下冰渣的稻田
穗芒如刺的麦地 豆地 高粱地
要钻红麻林 槐树林 枣树林 甘蔗林
爬陈梨山 左桃山 牛角山 高墙矮墙
要学会赤脚挑担走几十里山路赶集
腰不酸 脚不痛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赤脚积肥
掏粪坑 灶坑 污水坑 臭水坑
要习惯人粪 牛羊粪 猪马粪
鸡鸭粪 猫狗粪散发的各种气味
要耐得住苍蝇 牛虻 蚊子 小咬
蟑螂 老鼠 虱子 虮子 蝗虫的袭击
要学会亲近萝卜 白菜 黄瓜 土豆
珍惜每一粒米 每一把柴 每一根线
不吝啬每一滴汗水 心肠要软
腰身要硬 为人要厚道 手掌要有力
比如套牛犁田 耪地撒籽 浇水施肥
除草除虫 收割打场 脱谷扬糠……
这些都要会 车轻驾熟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享受
躺在地头睡觉的幸福 要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编竹筐竹篓 编草鞋笤条 织毛衣
男人 会修椅子锄头 磨镰炝刀
雨天用油毡纸砖头压实屋顶
女人 会烧饭洗衣 做针线 奶孩子 洗尿布
要喝井水 田沟水 吃糠麸 吃树皮
吃生瓜野果 野菜胃不疼
照样有力气 要习惯黑暗里走路
再黑的夜晚也能摸回家
死也要埋在自己的土地里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光着膀子
种庄稼 给家禽看病 给小羊 小牛接生
给猪狗 牛马配种 要习惯冬夜一家人
围坐火盆 灯下缝洗 积咸菜 说家常话儿
想打工在外地的亲人 不怕狼嚎 狗叫
要有飞蛾扑火的精神 习惯土坷
石头硌破脚底 手被庄稼勒出血道道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杀鸡 宰羊 剥皮
埋人 推碾子 拉磨 能忍受歉收荒年
没米下锅 衣衫单薄的煎熬 要会掰着手指过日子
要孝道 乐善好施 红白喜事要风光着办
要遵守村规家风 要会打肿脸装胖子 不能选择出身
不能屈服命运 要有一副老茧的肩头
忍住那些没钱治病的泪水……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要学会不低头 不埋怨
跪祠堂 跪娘亲 跪苍天
誓与土地共存亡 对一块土地
要有100%的信心与耐力 爷爷种60年
父亲种60年 你也要种60年
今天种 明天种 后天再种
种一百遍 一千遍 一万遍
人死地不闲
——做一个陈左湾村民
这是一首超容量的作品,在看似琐碎的絮叨里,其实是对中国农民命运及其文化心理的一次挖掘与梳理。苦难中的隐忍,隐忍中的守护,守护中的悲悯,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命运结构图,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提纲。那些在苦难中隐忍的农人,他们或许不知道什么是意义,但他们以自己脆弱而又坚实的肩膀,撑起了一个种族的繁衍,并使之生生不息。他们耕作,他们收获,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他们虚荣,他们忍气吞声,他们敬天敬地,然而,无论怎样,他们都没有屈服,而是像牲口一样,没有埋怨,也没有僭越,只是倔强地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者五谷,也耕耘着自己的人生。这是一首让人震撼的诗,它以集装箱一样密集的意象和情感,向我们展示了广大农村日常生活的波浪,以及更为隐秘但绝非虚构的心理潜流。
可以这样说,陈树照的诗歌从家乡出发,然后慢慢辐射,抵达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一种有根的写作。它扎根于承担了太多的泥土,并忠实于生长的规律,把生命瞬间的战栗、疼痛与幸福吟唱出来,给那片土地,也给自己的心灵。在我的阅读中,除去那些充满细节的家乡风物,他对现在生活的那片土地同样怀着深情。他写大雪,写得轻盈而多情,写雪中的人们,写得烟火气十足。所谓的故乡之外的“异乡”以及那种疏离的异乡情结,在陈树照的作品中是没有的。在他的情感版图上,没有地域的界限,也没有气候的划分,所有的价值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辽阔的感动与深沉的感恩。他是大地的赤子,是大爱的领受者与吟唱者,合着自己的节拍。
读他的作品,我经常会想起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或许可以这样说,陈树照的写作就是灵魂写作。因为,在当下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泥土的吟唱是低声的,它不可能超过那些娱乐至死的选秀,不可能超过那些真假难辨的花边新闻,它的听众不是大众,而是有沉重过去和当下关怀的少数人。所以,陈树照不在乎听者,只在乎自己的声音是否真诚,是否纯净。也正因如此,他的情感才有了更为细腻的和声,他的关怀才有了更为柔软的声部。
2012-4-28
作者简历:
辛泊平: 70年代生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星星》《雨花》《青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近百家报刊发表作品若干,并入选多种选本.作品被《读者》《中华文摘》(香港)等二十多家报刊及人民网、新华网转载,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现居秦皇岛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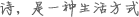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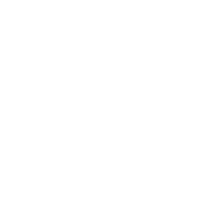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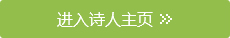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