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创作于2023年4月6日
让眸子在投屏的田园中悄然回放
口袁龙
拉出丝线的斜阳,
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路尽头悉数跌宕。
透过指缝的光亮,
跑到篱笆墙长长的缝隙处独自躲藏。
青山在陡峭的河崖下缺了掩饰,
一阵阵轻风,
把翠绿的柳丝吹送得扶摇直上。
季节在这个时候也在风口中游走,
藏在脑海中的岁月,
促使我的思绪有了轮回展播的欲望。
那是发生在多年以前的一件件往事,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都是我儿时在小山村永不走失的偶像。
那个时候,
奶奶总爱在星空下一遍又一遍给我讲述月亮婆婆的故事。
那架木制的纺车,
被她灵巧的双手抚摸得如同闪闪发亮的月光。
那个时候,
父亲常常爱叭哒着用竹节自制的叶子烟袋,
吐出一个接一个白色的烟圈,
好像东山坡上新雨后悠悠的白云一样。
母亲在那时没有过多的言语,
用茅茅草的余温煨出来的罐罐饭,
地道的稻米的香味,
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那个时候,
隔壁的二妞长得最为水灵,
两个红色的蝴蝶结,
春夏秋冬,
一直飘飞在我只想赞美只想仰慕的诗行。
那个时候,
走五里田坎路才能到达买到油盐的大队的推销店,
爬两座大山才能走到山丫处的公社小学堂。
行十里水路才看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坝坝电影,
如同雁阵的村民,
人人挑着晃悠悠的担子,
行二十多里路才能交售爱国的公粮。
那个时候,
还有柑橘花飘香时邻家二姐出嫁时的哭嫁歌,
麦收时春林哥在生产队宽畅的晒坝上迎娶松林寨的金凤凰。
那一件件刻骨铭心留下烙印的轶事,
都给我年龄越长乡愁越难忘的诗文中带来回放。
也许,这也是方言支撑着乡音,
乡俗承载着过往。
乡恋彰显着质朴,
乡思浸润着肝肠的真实写照。
融合的,是在时代的递延中不断上升的幸福指数。
点赞的,是绿水青山在故乡又成为金山银山的天堂。
如今,我又以回故乡哟忆故乡为题,
将眸子再度投屏于六十年间的过往。
山村中增添了无数的秀色,
走失的总是那些慈祥的脸庞。
从没有过的失落,
在这个春天开始不断翻捡不断疯涨。
我想,这也许也是血缘和亲情的碰撞,
让礼仪仁德的祖训,
有了继承和拓展的土壤。
那些曾经熟悉的人,
熟悉的场景,
一帧一帧地持续在脑海中投屏回放。
越过如烟的往事后,
大角度地,
揽尽了层林尽染的田园风光。
口袁龙
拉出丝线的斜阳,
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路尽头悉数跌宕。
透过指缝的光亮,
跑到篱笆墙长长的缝隙处独自躲藏。
青山在陡峭的河崖下缺了掩饰,
一阵阵轻风,
把翠绿的柳丝吹送得扶摇直上。
季节在这个时候也在风口中游走,
藏在脑海中的岁月,
促使我的思绪有了轮回展播的欲望。
那是发生在多年以前的一件件往事,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都是我儿时在小山村永不走失的偶像。
那个时候,
奶奶总爱在星空下一遍又一遍给我讲述月亮婆婆的故事。
那架木制的纺车,
被她灵巧的双手抚摸得如同闪闪发亮的月光。
那个时候,
父亲常常爱叭哒着用竹节自制的叶子烟袋,
吐出一个接一个白色的烟圈,
好像东山坡上新雨后悠悠的白云一样。
母亲在那时没有过多的言语,
用茅茅草的余温煨出来的罐罐饭,
地道的稻米的香味,
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那个时候,
隔壁的二妞长得最为水灵,
两个红色的蝴蝶结,
春夏秋冬,
一直飘飞在我只想赞美只想仰慕的诗行。
那个时候,
走五里田坎路才能到达买到油盐的大队的推销店,
爬两座大山才能走到山丫处的公社小学堂。
行十里水路才看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坝坝电影,
如同雁阵的村民,
人人挑着晃悠悠的担子,
行二十多里路才能交售爱国的公粮。
那个时候,
还有柑橘花飘香时邻家二姐出嫁时的哭嫁歌,
麦收时春林哥在生产队宽畅的晒坝上迎娶松林寨的金凤凰。
那一件件刻骨铭心留下烙印的轶事,
都给我年龄越长乡愁越难忘的诗文中带来回放。
也许,这也是方言支撑着乡音,
乡俗承载着过往。
乡恋彰显着质朴,
乡思浸润着肝肠的真实写照。
融合的,是在时代的递延中不断上升的幸福指数。
点赞的,是绿水青山在故乡又成为金山银山的天堂。
如今,我又以回故乡哟忆故乡为题,
将眸子再度投屏于六十年间的过往。
山村中增添了无数的秀色,
走失的总是那些慈祥的脸庞。
从没有过的失落,
在这个春天开始不断翻捡不断疯涨。
我想,这也许也是血缘和亲情的碰撞,
让礼仪仁德的祖训,
有了继承和拓展的土壤。
那些曾经熟悉的人,
熟悉的场景,
一帧一帧地持续在脑海中投屏回放。
越过如烟的往事后,
大角度地,
揽尽了层林尽染的田园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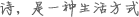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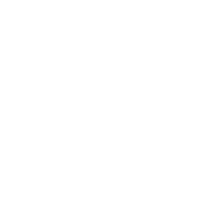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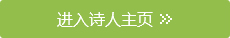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