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惊蛰,百虫苏醒, 布谷叫响,春耕来临。 转眼,迎来四月清明, 迎来踏青、放风筝、祭祖扫墓的江南风俗, 迎来肉粽、枣粽、青团子、麦芽饼冲击饥饿胃口的美丽时节。
春暖花开,燕子归来,斜飞如织。 屋檐下,燕儿呢喃我童稚的许多梦想。 于是,我用羊毫毕恭毕敬地写下我的梦想, 搬着小凳贴上自家过庐(吃饭间)的板墙。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在春风唤醒蝌蚪、暖阳叫人慵懒的日子里, 去乡野看一看大片大片点头含笑的兴奋摇曳的麦芒, 去吻一吻大片大片金黄的令人沉醉的油菜花香, 去听一听无数的嗡嗡嘤嘤的小精灵——蜜蜂的吟唱, 内心的欢快似渠水涓涓地流向远方。 尔后,便是端午。 艾叶菖蒲斜挂门上,桃梗蒜头悬于床户, 驱邪却鬼,佑我安康。
在黎明,晨曦初露。 炊烟洁白,袅袅飘荡。 屋旁的苦楝树一语不发, 而泡桐树上鹊叫清脆。 出笼的鸡鸭扑棱着翅膀。 鸭叫嘎嘎,大步摆向小河; 鸡啼嘹亮,四散觅食野外。
每当夕阳西下,坐在垄上, 看老父甩开膀子在自留地上翻垦种植, 感觉生活就是这样, 质朴如土,温饱可依,踏实安宁,田园流芳。 而每当看到父亲哮喘吁吁, 严重时咳出血来的情景, 孩儿又会忧心如焚, 恍如天空不再灿烂温煦,黑压压地乌云密布。 在饭后的黄昏,看爷爷坐在门槛, 旱烟用火柴划燃,星火如萤虫闪亮。 记忆里,爷爷睡梦里总是哼着山歌,老把我们唱醒, 总是风雨无阻地一大早去街上零卖自己侍弄的时鲜蔬菜,换回每天开销。 喝完早茶回来,总买回零食小吃, 特色熟食(麻球、茶糕、羊饺等),还有时令水果。 可见,爷爷对小孙子的宠爱有多深。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老家总是一个可安心停泊的港湾。 老屋虽旧,但温馨暖人叫人眷恋。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 草窝孕育幼小生命; 草窝深藏乡风淳朴; 草窝遗传倔强个性; 草窝培养老牛品格。 老家希望破土,似雨后春笋。 灶旁的水缸映照阿姐粉红的脸庞, 门前清澈的河面映现天空的美丽。
“绿树浓荫夏日长”。 每当夏天到来,听蝉叫是一种诗意悠然, 那是没有烦躁的童稚心境。 用蛛丝去粘捕老蝉只是儿时的作业, 那是闲不住的夹带破坏欲的天真。 炎热的午后,南风轻拂, 乡村气息如蒸南瓜一般糯甜, 也似一钵甜醇的酒酿。 七、八月的江南,骄阳似火。 儿时,我对“双抢”①大忙季节父老乡亲的劳苦劳力,真没有很深的体验。 只是知道父母姐姐越热越是不见人影, 天不亮就去上早工,天乌黑还得开夜工。 清晨,大人一走,我就知道哇哇地哭, 傍晚,浑身上下被蚊子叮咬,又嗷嗷地叫。 长大后,自己亲自参加“双抢”了, 才知道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炼狱, 我要向那些披星戴月满身臭汗、〝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卑微而又伟大的劳苦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真的,在“大呼隆”年代, 夏季确乎是黑色的, 农忙是残酷的抢夺式的, 这个农忙,是乡亲们咬紧牙关向着自己的生理极限、抢种时节所发起的一年中最为严峻的挑战! 而如碾重负,似乎要磨碎他们善良朴素的生存意志。 你们,就是你们,扛着不堪承受的重, 浅一脚深一脚地犁耕在漠漠的田野。 而我因为懵懂,自然不解勤劳致贫的原因, 因为幼小,只能跟邻居小孩抱团作伴, 翘着二郎腿惬意地躺在藤椅上, 把暑期唱成一首轻松明快的歌!
诚然,儿时的清贫如夏夜的蚊虫,任你摇着蒲扇拍赶都驱之不走,这是代际的命运。 我终于懂得了一天早晚两顿稀粥的幸运含义, 懂得了酱油、萝卜条、咸菜、补丁、稻草、木炭、光棍的含义, 懂得了票证的身份象征与经济价值。 但穷开心仍在, 无论吃着从生产队分到的黄灿灿的香瓜 或嚼着有滋有味的松脆的油炸豆瓣, 还是在大队小学的泥地操场带着过节心情 观看诸如《小兵张嘎》、《地道战》这样的露天黑白电影; 也无论躺在纳凉门板上仰望星空亮晶晶, 还是听老人们讲那长毛或志怪故事, 还是跟赤膊小朋友一道,围观 相互叫着“麻子”、“卵毛”、“癞痢”、“白肚”诨名的 小伙子力量的比试——扳手腕, 抑或去乡场做着属于孩子们的自编自导的游戏……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秋天。 而我的秋天,总是芦花迎风摇,寒气侵衣冷。 早晨起床,定会看到一片雪白的霜降。 稻穗遗落田畴,孩子们总在大人们的怂恿下纷纷下田捡拾, 现在想来这是对的。 这是在捡拾一种千年传承的朴素的勤俭的美德, 这画面一定美得珍贵, 美得叫人淡淡忧伤, 美得叫人肃然起敬!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 到了冬天,能在墙旮旯晒着暖阳的大概只有老人和小孩。 到了冬天,母亲那双操劳的手注定是布满冻疮的皲裂的, 那是一双缝补浆洗的手, 一双把持四个孩子学会走路的手, 一双从不间断田间劳作的手, 一双月子只坐了两天就下田拔秧的手。 每当雪霰从瓦楞或北窗的缝隙簌簌飘落, 就想起母亲温暖的怀, 就想到母鸡用体温窝着一群鸡雏的本能的爱。 严寒,让我想起铜火炉的温暖, 想起灶膛煨番薯的香甜, 想起屋檐下垂挂的长长的冰凌, 想起一片皑皑白雪下一年中最难得的闲—— 最享受的虽苦犹乐的时光。 在腊月年关,只要小队“共育房”②门前 临时垒砌的土灶里桑柴燃起, 蒸笼上喷香的蒸汽氤氲飘荡, 便知家家合伙打年糕了,过年气氛渐浓。 腊月廿三,吃赤豆糯米饭。 转眼,除夕到了,吃年夜饭之前, 孩儿总急不可耐地用脏兮兮的小手撮着 老爸刚从腌猪头上使劲卸下来的颊骨肉, 热乎乎香喷喷地啃起来。 饭后数着崭新的几角压岁钱,开心地出门去。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想到明天是大年初一, 除夕这一宿居然兴奋得横竖睡不着。 一清早,母亲准会各送两颗粒糖到枕边, 并叮嘱儿女睁开眼便要甜甜嘴。 捱到阳光照进木窗,再也按捺不住, 在被窝里一个劲地嚷着新棉袄新棉裤新袜子新鞋子。 起床后,喝过糖汤、吃过顺风汤圆, 穿着母亲平时在昏黄如豆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成的新鞋, 兴高采烈地跟随爷爷步行去镇头走亲戚。 客人一到,主人又是沏茶, 又是拿出糖果、瓜子、花生、核桃客气招待, 照例叫吃每人汤包一客。 开饭了,主人会摆上满满一圆桌丰盛的炒头, 那真叫胃口大开,不知客套为何物。 走上一走江南古镇的石板路, 到处感受到过年的那份特有的喜气, 人群熙攮,爆竹声声, 意识到自己又长大了一岁, 过年的纯正,叫人难以忘怀。
呵呵,我童年快乐的足迹遍布我的村庄。 我的童趣就在捣鸟窝、翻筋斗的竹林里; 就在摸螺钓虾的河湾里; 就在坐在门前的竹椅上学吹《浏阳河》的竹笛里; 就在红色的语录标语口号里; 就在学唱高音喇叭重复播放的革命样板戏的经典唱段里; 就在批孔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漫画习作里; 就在篱笆边野桑下野火饭的炊烟里; 就在抽陀螺、捉迷藏、打弹弓、荡秋千、堆雪人的贪玩的天性里……
逝者如斯,人世沧桑。 我怀念已故的叫我崇敬的劳苦了一辈子的亲人。 爷爷的老坟在小河南岸的桑林, 父亲的新墓地在庙西的高地。 他们终日守护着这片庄稼, 守护着这片最稔熟不过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 他们的魂魄永在那儿, 连同我儿时记忆中的村庄,永不磨灭。 想起儿时村庄, 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念想, 一切的一切,永永远远亲切如常!
春暖花开,燕子归来,斜飞如织。 屋檐下,燕儿呢喃我童稚的许多梦想。 于是,我用羊毫毕恭毕敬地写下我的梦想, 搬着小凳贴上自家过庐(吃饭间)的板墙。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在春风唤醒蝌蚪、暖阳叫人慵懒的日子里, 去乡野看一看大片大片点头含笑的兴奋摇曳的麦芒, 去吻一吻大片大片金黄的令人沉醉的油菜花香, 去听一听无数的嗡嗡嘤嘤的小精灵——蜜蜂的吟唱, 内心的欢快似渠水涓涓地流向远方。 尔后,便是端午。 艾叶菖蒲斜挂门上,桃梗蒜头悬于床户, 驱邪却鬼,佑我安康。
在黎明,晨曦初露。 炊烟洁白,袅袅飘荡。 屋旁的苦楝树一语不发, 而泡桐树上鹊叫清脆。 出笼的鸡鸭扑棱着翅膀。 鸭叫嘎嘎,大步摆向小河; 鸡啼嘹亮,四散觅食野外。
每当夕阳西下,坐在垄上, 看老父甩开膀子在自留地上翻垦种植, 感觉生活就是这样, 质朴如土,温饱可依,踏实安宁,田园流芳。 而每当看到父亲哮喘吁吁, 严重时咳出血来的情景, 孩儿又会忧心如焚, 恍如天空不再灿烂温煦,黑压压地乌云密布。 在饭后的黄昏,看爷爷坐在门槛, 旱烟用火柴划燃,星火如萤虫闪亮。 记忆里,爷爷睡梦里总是哼着山歌,老把我们唱醒, 总是风雨无阻地一大早去街上零卖自己侍弄的时鲜蔬菜,换回每天开销。 喝完早茶回来,总买回零食小吃, 特色熟食(麻球、茶糕、羊饺等),还有时令水果。 可见,爷爷对小孙子的宠爱有多深。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老家总是一个可安心停泊的港湾。 老屋虽旧,但温馨暖人叫人眷恋。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 草窝孕育幼小生命; 草窝深藏乡风淳朴; 草窝遗传倔强个性; 草窝培养老牛品格。 老家希望破土,似雨后春笋。 灶旁的水缸映照阿姐粉红的脸庞, 门前清澈的河面映现天空的美丽。
“绿树浓荫夏日长”。 每当夏天到来,听蝉叫是一种诗意悠然, 那是没有烦躁的童稚心境。 用蛛丝去粘捕老蝉只是儿时的作业, 那是闲不住的夹带破坏欲的天真。 炎热的午后,南风轻拂, 乡村气息如蒸南瓜一般糯甜, 也似一钵甜醇的酒酿。 七、八月的江南,骄阳似火。 儿时,我对“双抢”①大忙季节父老乡亲的劳苦劳力,真没有很深的体验。 只是知道父母姐姐越热越是不见人影, 天不亮就去上早工,天乌黑还得开夜工。 清晨,大人一走,我就知道哇哇地哭, 傍晚,浑身上下被蚊子叮咬,又嗷嗷地叫。 长大后,自己亲自参加“双抢”了, 才知道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炼狱, 我要向那些披星戴月满身臭汗、〝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卑微而又伟大的劳苦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真的,在“大呼隆”年代, 夏季确乎是黑色的, 农忙是残酷的抢夺式的, 这个农忙,是乡亲们咬紧牙关向着自己的生理极限、抢种时节所发起的一年中最为严峻的挑战! 而如碾重负,似乎要磨碎他们善良朴素的生存意志。 你们,就是你们,扛着不堪承受的重, 浅一脚深一脚地犁耕在漠漠的田野。 而我因为懵懂,自然不解勤劳致贫的原因, 因为幼小,只能跟邻居小孩抱团作伴, 翘着二郎腿惬意地躺在藤椅上, 把暑期唱成一首轻松明快的歌!
诚然,儿时的清贫如夏夜的蚊虫,任你摇着蒲扇拍赶都驱之不走,这是代际的命运。 我终于懂得了一天早晚两顿稀粥的幸运含义, 懂得了酱油、萝卜条、咸菜、补丁、稻草、木炭、光棍的含义, 懂得了票证的身份象征与经济价值。 但穷开心仍在, 无论吃着从生产队分到的黄灿灿的香瓜 或嚼着有滋有味的松脆的油炸豆瓣, 还是在大队小学的泥地操场带着过节心情 观看诸如《小兵张嘎》、《地道战》这样的露天黑白电影; 也无论躺在纳凉门板上仰望星空亮晶晶, 还是听老人们讲那长毛或志怪故事, 还是跟赤膊小朋友一道,围观 相互叫着“麻子”、“卵毛”、“癞痢”、“白肚”诨名的 小伙子力量的比试——扳手腕, 抑或去乡场做着属于孩子们的自编自导的游戏……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秋天。 而我的秋天,总是芦花迎风摇,寒气侵衣冷。 早晨起床,定会看到一片雪白的霜降。 稻穗遗落田畴,孩子们总在大人们的怂恿下纷纷下田捡拾, 现在想来这是对的。 这是在捡拾一种千年传承的朴素的勤俭的美德, 这画面一定美得珍贵, 美得叫人淡淡忧伤, 美得叫人肃然起敬!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 到了冬天,能在墙旮旯晒着暖阳的大概只有老人和小孩。 到了冬天,母亲那双操劳的手注定是布满冻疮的皲裂的, 那是一双缝补浆洗的手, 一双把持四个孩子学会走路的手, 一双从不间断田间劳作的手, 一双月子只坐了两天就下田拔秧的手。 每当雪霰从瓦楞或北窗的缝隙簌簌飘落, 就想起母亲温暖的怀, 就想到母鸡用体温窝着一群鸡雏的本能的爱。 严寒,让我想起铜火炉的温暖, 想起灶膛煨番薯的香甜, 想起屋檐下垂挂的长长的冰凌, 想起一片皑皑白雪下一年中最难得的闲—— 最享受的虽苦犹乐的时光。 在腊月年关,只要小队“共育房”②门前 临时垒砌的土灶里桑柴燃起, 蒸笼上喷香的蒸汽氤氲飘荡, 便知家家合伙打年糕了,过年气氛渐浓。 腊月廿三,吃赤豆糯米饭。 转眼,除夕到了,吃年夜饭之前, 孩儿总急不可耐地用脏兮兮的小手撮着 老爸刚从腌猪头上使劲卸下来的颊骨肉, 热乎乎香喷喷地啃起来。 饭后数着崭新的几角压岁钱,开心地出门去。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想到明天是大年初一, 除夕这一宿居然兴奋得横竖睡不着。 一清早,母亲准会各送两颗粒糖到枕边, 并叮嘱儿女睁开眼便要甜甜嘴。 捱到阳光照进木窗,再也按捺不住, 在被窝里一个劲地嚷着新棉袄新棉裤新袜子新鞋子。 起床后,喝过糖汤、吃过顺风汤圆, 穿着母亲平时在昏黄如豆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成的新鞋, 兴高采烈地跟随爷爷步行去镇头走亲戚。 客人一到,主人又是沏茶, 又是拿出糖果、瓜子、花生、核桃客气招待, 照例叫吃每人汤包一客。 开饭了,主人会摆上满满一圆桌丰盛的炒头, 那真叫胃口大开,不知客套为何物。 走上一走江南古镇的石板路, 到处感受到过年的那份特有的喜气, 人群熙攮,爆竹声声, 意识到自己又长大了一岁, 过年的纯正,叫人难以忘怀。
呵呵,我童年快乐的足迹遍布我的村庄。 我的童趣就在捣鸟窝、翻筋斗的竹林里; 就在摸螺钓虾的河湾里; 就在坐在门前的竹椅上学吹《浏阳河》的竹笛里; 就在红色的语录标语口号里; 就在学唱高音喇叭重复播放的革命样板戏的经典唱段里; 就在批孔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漫画习作里; 就在篱笆边野桑下野火饭的炊烟里; 就在抽陀螺、捉迷藏、打弹弓、荡秋千、堆雪人的贪玩的天性里……
逝者如斯,人世沧桑。 我怀念已故的叫我崇敬的劳苦了一辈子的亲人。 爷爷的老坟在小河南岸的桑林, 父亲的新墓地在庙西的高地。 他们终日守护着这片庄稼, 守护着这片最稔熟不过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 他们的魂魄永在那儿, 连同我儿时记忆中的村庄,永不磨灭。 想起儿时村庄, 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念想, 一切的一切,永永远远亲切如常!
注释:
①“双抢”指双季稻的收割与栽插,时间大概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
②“共育房”指用以养蚕的集体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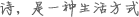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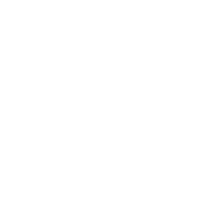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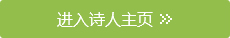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