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谨以此诗,献给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巴山区父老乡亲
巴山老房子
(叙事诗) 向求纬
谨以此诗,献给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巴山区父老乡亲
——题记
第一章 大巴山腰间的一个胎记
老房子在山上
大巴山南麓之一隅
当初川陕两省交界处
后来渝川陕三省交界处
离陕西近
五六十里就跨过界梁
离四川更近
二三十里就赶钟亭的乡场
可离县城远啊
130里路还隔着一条大河三座大山
老房子在山下
群山环绕的一个低凹处
由东向西倒流的任河
远远地流来
快出县境也就是快出省境了
在这儿拐了个大弯
把这座老房子和老房子们
挽在怀里慢慢地诳
久久地哄
白日夜晚
千年百载
不知睡着没有
不知睡醒没有
大巴山长在腰间藏着掖着的一个胎记
老天朝下看看得见它
世人四处看看不见它
城市走瘸了腿好久也走不近它
那个叫做“现代文明”的娃娃
投错了胎也一时半会投不进这里来
老房子其实很富有啊
四周那山 那岩 那林 那草
面前这土 这地 这河 这水
随便薅上一把都能冒油
都能变金 变银
本来就在福窝窝里躺着哩
抓一把风来轻轻一吹
也能像孙猴子一样要啥变啥
可这块土地却穷得舔灰呀
穷得鬼都不愿生蛋
成年累月 风雨飘摇
子子孙孙 没完没了
重复着一副似曾相识的情景——
超生的娃娃们蜷曲在灰坑旁
一群不辨眉眼的灰老鼠
掏着抢着剥着烧熟的种洋芋
一个个吃得口水滴嗒的
大人们藏在成堆的包谷壳里
赤身露体
(报上曾有过“牛吃‘铺盖’”的说法)
一家一条公用的“油渣裤”
谁出门谁穿
老人们躺在无药可医的篾巴折床上
听着天由着命
病病哀哀地成天发愁
地里是朝天一把籽坐地等花开
小包谷挨着地长成“野鸡啄”
麻洋芋不等成熟就被“阉割”提前当口粮
红苕只长藤叶根须儿却不结大疙瘩
无油无盐的日子
油就免了 最要命的是缺盐呀
上了点年纪的巴山人
脖颈上多半吊着一只大瘿包
一把羊角锄
起呀落呀挖呀掘呀
水流了 山秃了
土瘦了 人老了
做也做了 干也干了
苦也苦了 累也累了
何时能饱腹
何时能蔽体
何时是个头?
贫困埋的根
贫困惹的祸
贫困遭的罪
贫困作的孽
历史留下的一层皮
到底能不能蜕下来?
根深蒂固的一位“阿斗”
到底能不能扶起来?
第二章 老房子蹲在三省交界处
老房子是一群房子
茅草盖顶 石瓦盖顶
黄泥筑墙 石块砌墙
整体坐北朝南
个体却杂乱无章
有房子必有一孔猪圈
秸秆垛木 天穿地漏
雨天钻个人进来解便
背湿得很哪
包谷壳还老是揩不干净
老房子是一群人
二三十家 百十口子
当家人统统姓冉
(要不然面前的场镇怎么叫冉家坝呢)
都说“冉家坝的布染不得”
老房子真没人惹得起哟
同胞兄弟 隔房姐妹
同天同地 同天异地
地坝边上一棵石榴树
年年结金果
岁岁抱成团
你锅里有我碗里有
你抱肚子饿我也不饱腹
同宗的血脉祖传的豪气
吃一起 住一起
穷一起 苦一起
倘能富呢
是不是也能在一起
没听说贫困与海拔有关
三位数的海拔
老房子却比四位数幸运
好在近处有一些坡地
好在远处有一些荒地
任河那低低的臂弯里
一条猪屎河流过去
一条猪屎街算是场镇了
这样老房子就算是近郊了
靠着河靠着街是最大的优势
关键还有一点水田
稻谷刚好够交公粮
够帮助国家吃上一口田米(大米)了
够帮助公家人吃上一顿田米了
够自家过年的时候尝尝米饭味道了
(那可是大人细娃盼星星盼月亮的团年饭哪
连刨七口才睁眼睛呢)
这可比四周高山农家强多了
没听说“高山老二下不得河
下河就是棕包脚
烤的是转转火
吃的是洋芋果
喝酒吃肉好家伙
栽秧搭谷奈不何
要想吃一颗田米儿
转世投胎重来过”
老房子个个人勤快啊
男人种地 女人摘茶
纵是苦日子也算计着过
出门风都要抓一把
走路也要采一兜猪草
清晨打早工开荒地
回来带回一捆柴
肚子都还咕咕叫呢
猪头牲口就打圈了
紧赶着又要出门上工
搅一顿包谷糊糊将就喝了
生产队站成“翼口”(干活的队列)挖地
歇气了
妇女抓起奶子朝后一甩
背上的娃娃就捉住进食了
要不然将娃娃搁在茶树蔸下
让他和蚂蚁蚯蚓玩耍
有时还有一条小蛇儿光顾
娃娃从不知道啥叫害怕
这大巴山就用羊角锄这么挖着
这任河水就让奶娃娃这么背着
通向山外的小路就让几个背二哥走着
陕南的风 川东北的风
途经此地赶紧一抹而过
忙早忙晚 累死累活
包谷面糊都喝不饱啊
春荒时节还得打蕨根哩
老房子的土墙石瓦
盖着蹲着有些不安生了
这哪儿是个事啊
坐牢房还有个期限呢
(还别说真有个孤儿
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想去坐牢
去住不要钱的房吃不要钱的饭)
这铁桶一般的大山
这可怜的一亩三分田地
这林海树海花海草海包裹的苦海
何时才能触底反弹
何时才能靠边登岸
后来山林田地分下了户
这日子就缓过一口气来
再不在生产队排队干活
出工就指望太阳落
锄把老杵着都长了老木菌了
劳动力多 劳动果实少
浑身的劲儿没使出
一身的疙瘩肉没结出疙瘩
这人哪 真是贱相
大锅饭吃着老吃不饱啊
小锅小灶喝面糊也觉着香
春耕时节——
犁田了 打耙了
你借我的牛
我借你的耙
小小稻田像经佑幺儿
一遍遍耱得个油光水滑
栽秧了 播种了
一群群一家家换工了
嫩胡豆下着栽秧酒
山歌唱得呵吙连天地响
秋收时节——
你家扛来大拌桶
他家背来大背篼
嚓嚓嚓嚓割呀割呀
嘭咚嘭咚搭呀搭呀
散开的谷把子放倒在地
合拢的谷把子一飞冲天
这单干才有劲哟
这合作才有力哟
山林田地承包50年不变
半个世纪的收成
看似不多年年有
一瓢一勺不流外人田
咱祖辈的农民图个啥呢
地里有刨的
锅里有煮的
身上有穿的
膝下有逗的
一日两餐不断顿
(农家开饭是二五八)
就够了 就足了
不盼了 不想了
第三章 “大背老二”带来了“电影气气”
远近闻名的冉氏宗族
老一辈一个个撒手而去
在老房子背后的楠竹林里躺着
让后阳沟共用的一眼泉水
滴着冬冷夏凉的泪
老二辈也老了
白头巾青布衫裹着
铜头长烟杆杵着
走来走去 磕来磕去
后生们也不大搭理了
“变了泥鳅就得钻土”呀
“头上蒙块布把着活路做”呀
这祖训听着也有些腻了烦了
老三辈们正当年呢
精力旺盛 想入非非
这日子不能这样过下去了
走出去 跑出去
看看山外啥模样
听听山外啥响声
听说这地球大得很哩
难不成都跟这山里一样光景
年轻人正这样想着
驻村干部来了
都是些书记呀社长呀武装部长呀委员呀
每人包干一两个村
都是庄稼人出身
本乡本土的
干工作做事情没挑剔的
喝酒吃肉也很在行
酒杯一端
就有些云天雾地的了
就有些口无遮拦了
老房子尽是些机灵鬼哟
日子再紧
这穿肠过的东西随时攒着
(老房子就是驻村干部的伙食团呢)
地坝里摆上酒壶土碗
几块洋芋片几颗炒黄豆就可佐酒
实在不行就烟下酒酒下酒龙门阵下酒
肚里一发烧
舌头就不灵活了
话匣子就打开了
想挣点油盐钱么
想甩脱穷皮皮么
年轻人是得往外跑哩
这石骨子坡坡肯定挖不出金娃娃来
山外的月亮比这儿都大
山外的票子比这儿都长
还有山外的女娃子
嘻嘻,比这儿都……
不过话又说回来
找出路 先修路
一步路都走不伸展
天大的想法有什么用
地大的本事有什么用
县里有计划
专区有计划
省里有计划
国家有计划
这冉家坝要修公路了
本县的大山
怕是世袭的骨头太硬吧
这路要从外省绕道来……
出门要修路
挣钱先修路
铁桶般的大山严丝合缝
咱要让它裂开一条缝
破开一道口
让鲜活的空气透进来
让折射的阳光探进来
让新奇的图景映进来
让崭新的希望照进来
论修路
老房子有的是劳力
老房子有的是内行
陈氏宗族的活先人发一声喊
山山岭岭都回应
公家来修路
私人打帮手还不行么
有人出人
有力出力
有物出物
个别有钱的还得出钱哩
规划线路上有个垮石湾
坚硬的岩石一点不垮
拦路虎呀 老大难呀
工程技术人员着了急
别慌
老房子有个高中生
平日里喜好摆弄点机械呀雷管磺药什么的
自学成才的能工巧匠
这小子来到垮石湾
和技术员厮守在一起
山梁上比划
图纸上勾描
跑县里蹲图书馆
去水电局请教技师
这一天来了个人员大撤离
放上警戒望上风
就在这千年沉闷的僻静处
震天动地一阵炮响
定向爆破成功了
垮石湾名副其实了
这老房子的回乡青年
还真有点接生婆戴眼镜——
看你娃娃不出来!
说话之间好快呀
路来了 路通了
川陕交界处来了个弯弯绕
跨县跨市跨省地过来了
不大宽的路
不大平的路
(可那是盘古开天地的路啊)
通车典礼的横幅挂出来了
十余辆汽车披红挂绿
鼓着眼睛 喘着粗气
挪过来了 挪过来了
山上的老农下来了
祖传的小脚 过年的新衣
扶着搀着下来了
界梁那边的老农过来了
背着干粮 备着火把
也想来沾一点喜气呢
谁见过这样的“大背老二”呢
不喝酒 不吃粮
拉货几吨十几吨
这得俯下身子看个仔细才行
这家伙到底是公是母?
老房子有个电影放映员
天天柴油机一响竖起大银幕
这会儿煞有介事了:
大家闻闻大家闻闻
这大背老二好大一股电影气气!
这电影气气扩散的地方
喇叭一响 黄金万两
大巴山一隅的第一条公路
窄是窄点
弯是弯点
糙是糙点
绕是绕点
(进县城还得出省界呢)
可打通了血脉连上了筋
自个儿心爱的就是宝啊
走人户呀 串亲戚呀
背力呀 搭车呀
跑车呀 运货呀
就开个手扶拖拉机也神气啊
突突突突像个土皇帝
人不熟悉也不得刹一脚哩
还有闲人也出门瞎逛逛了
顺着公路 指点江山
(这怕是后来“旅游”的前身?)
是呀 是呀
这就近的景点这么多
眼皮子下的风景这么美
往时为啥就看不见呢
为啥就走不拢去呢
谁说灯下黑呀
这桐油灯马灯煤油灯电灯底下
那可是多乖多亮堂呢
第四章 任河拐了一个几字弯
面前就是一条河
那可不是大巴山第一条河
自东向西倒流三千八百里
千年百年地流来
悄没声息地流来
流进汉水 注入长江
流得大巴山多年未见异常
流得冉家坝多年未见异常
流得老房子多年未见异常
只是灌了点好田地哟
河水挑来
干涸的土地好歹止一下渴
没力气开渠筑堰啊
天干时节
为争一口沟水
亲兄弟也打得头破血流
只在河里打了些好鱼哟
夏夜
鱼鳖们趴在沙滩上乘凉
提个马灯
一个一个只管往篓子里捡
秋晨
拎一部电话机来到河边
两股电线丢进水里
一阵猛摇
无鳞的鱼儿禁不住电话骚扰
晕头转向窜上来
钻进长竹竿的网兜里
趁着没人的时候
一坨炸药丢下河
鱼儿散浮一片
饱了口福
许多楞小子却成了永远的“一把手”
两三层楼深的绿荫潭里
憋着气钻下去摸鱼
上呀 下呀
钻呀 摸呀
一把鼻血染了绿水
一条大鲢鱼换了些零用钱
这河里的娃娃鱼可惹不起
那是送子娘娘设下的诱饵呢
捉了那鱼会断子绝孙的
可街上的脱产干部才不管那么多哟
炖一罐鱼汤美滋滋地喝
咳 不吃白不吃
山民也要顾嘴巴了
哪管下一代断后不断后
只在河里放了些好木柴哟
峭壁上树棒扔下河
牛麻藤 做绳索
翘紧了 打成捆
一根泡桐树做托柴
掀进河里漂下来
漂到回湾处
正好 捞上来
分成小捆
一趟一趟扛回家
坝里的土瘦了
山上的树光了
河里的鱼少了
老房子的炊烟
冉家坝的炊烟
四山的炊烟
你又能维持得多久
靠山越靠山越空
靠水越靠水越枯
光阴不再
山水不言
老家的山你难道真的不怜人
故乡的水你难道真的不动心
第五章 山外的月亮大又圆
说去说来
还是老房子的年轻人脑瓜儿灵光
多读了几天书
成天想精想怪地想
先是在院坝里牵一根线线
弄来个木匣子挂着
咿咿呀呀地唱起了秦腔
这可稀罕得很哪
后山下来的老农
叼着烟杆转来转去地看
这个把戏了不得呀
那么小个箱箱儿
哪儿装得下那么多人
一个个还嘶声瓦气地唱 唱
后来老房子又弄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叽哩哇啦地说呀 叫呀
这东西就更神奇了
拿在手里的一块“砖头”
连绳索都不牵一根
它还有精神叫?
还有精神嚎?
老房子可不管那么多
只管打自己的主意
这路也通了
信息也来了
年轻人哪还待得住啊
一颗心早飞出了家门
飞出了山门
飞到东南沿海去了
听说那边海风那个呼啸呀
海潮那个汹涌呀
到处想见个山包包都难哩
哪来这么多的大山
那儿的土地又平又宽
哪像我们这边
巴掌宽个地势都叫做“坪”
簸箕大块平地都叫做“坝”
出门去 出门去
出山去 出山去
见一片世面挣几个钱
回来孝敬父母
回来娶个媳妇
回来砌个新房
回来置办家产
冉老三的幺儿邀上几个人
去了东莞一家玩具厂
从小都没玩过玩具
如今玩具堆成山
那个新鲜呀
那个快活呀
这活路比挖地可轻松一半呢
这活路比挖地可划算一倍哩
没过几年
冉老幺炒了那老板
自己牵头造玩具
叫来老房子七大姑八大哥
开了个家族玩具厂
我玩大玩具
你玩小玩具
他玩玩具小部件
几玩几不玩
咦,不愧是老房子出来的灵醒人
腰包多少都鼓了起来
腰杆多少都粗了起来
过个年呀回个家呀
都学着光起宗来耀起祖来
哼 一样的包谷米吃着长大
他老房子凭啥就能发财
新房子旧房子高房子矮房子草房子木房子
都是人 都长手
都出去 都打工
谁都能混出个人样来
这一下悬崖裂了口
洪水开了堤
大巴山拥出了打工仔
四面八方 排山倒海
那个贪婪劲
那个勤劳劲
那个拼命劲
那个聪明劲
要个人来赶哪要个人来赶
可十根手指扯不齐呀
一胞鸡崽不是个个都会叫哩
本以为山外遍地是黄金
却原来条条蛇儿都咬人
冉老七的大儿邀了几个人去灵宝
听说那儿沙里能淘金
捏一把满手都淌金水哩
谁料到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苦功花不开
金沙才不认偷懒鬼呢
沙里淘金 你得用力淘呀
你得流汗水呀
没法子 心生一计
拦在半路上 抢他两个金老板
完事跑进大巴山
找一处老房子躲起来
冉幺爷为这事可是动了气啊
没见你这么打工的
没见你这么挣钱的
不成器的东西
咱冉家怎么养出了这种货色
国法未动家法动
来来来
罚你在神龛前跪三天
水米不沾牙
无令不起身
看你还当不当棒老二
看你做人还像不像人
江河毕竟东流去
节令到了挡都挡不住啊
远处能打工 近处也招工
县里砖瓦厂
区里供销社
乡里加工厂
老房子当仁不让啊
有指标就去
有空子就钻
有活路就做
谁会跟挣钱过不去呢
可挣钱也得有准备啊
挣钱也得有资格呢
初踏脱贫路
还真是五花八门丑态百出
生产队工分记惯了
如今拿工资
诚惶诚恐 藏着捏着
生怕别人看见了
还有人花都不会花
数都不会数哩
冉老九家的三女子
模样长得好
就是读书不用功
好容易跨进学校门
上了些“瞌睡课”
读了些“滑水书”
混了个初中二年级
斗大的字还写不出几个
这次招进了食品站
社员要杀猪
要开屠宰证
冉三妹你给开开吧
堂堂中学生呢
开完拿过来一看
天哪
屠宰种类一栏里
赫然填上社员老爹的名字
这可把社员惹毛了
宰你个老房子亲爹爹哟
你老房子个个都是猪!
一场祸惹得可不小
唇枪舌战 恶语相向
差点儿还动了干戈
说起来令人可叹哪
祖祖辈辈穷惯了
没文化真是不行啊
送去读书吧
送去读书吧
女娃娃多半没这资格
男娃娃都是些二杆子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混几年 混几年吧
认得到钱 认得到秤
能写自己名字就行了
就这还有人不达标呢
那年陕西过来个生意客
一叠崭新的袜子商标
就“买”走了这边的一口袋天麻
还有人用嵌磁铁的秤
称走了成捆的茶叶
难怪学校老师都笑说
别看老房子那些小子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啊
此言过了
此言差矣
老房子算是周遭的佼佼者呢
你看四周老山上
常有些呆儿傻儿下来
见人流着涎水瘮人地笑
满街追打花衣服
满身污垢 衣不蔽体
让人看着好心酸
可眼下路开了 山开了
天开了 云开了
一苗露水一苗草
一只老鸹一片滩
人生在世都有道理
人活着都有他的生路呀
吃饱饭的机会
穿新衣的机会
余钱剩米的机会
过好日子的机会
只要活着眨眼的 喘气的
纵是在这两省交界处
在这冷僻窎远处
在这贫困潦倒处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啊
第六章 一颗明珠落深山
还得说这一条古老的任河
巴山人再老也老不过它
它流赢了 流老了 流走了
那它转个弯干啥呢
直端端流过该多好
它有心啊 有意啊
千百年来的心思
它不说
它不折腾
它让你去猜 去想
连老房子都弄不明白
它隔着一道山梁
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干什么
天看着知道
树围着知道
岩立着知道
风擦着知道
那河水要有大动作
那河水不愿平躺着
那河水出乡出县出省的时候
不会白白地就这么走掉
说时迟 那时快
有朝一日
这河水来了个急刹车
这河水忽然间腾身而起
这河水在山梁间冲开了个洞
这河水再不走弯路了
再不静默无声了
它要对对直直地出乡 出县 出省
它不满足于浇几块田地养几根山柴喂几条鱼儿了
它要如电光石火
如霹雳雷电
如雨露甘霖
如大道通衢
它要变身 变脸 变形 变色 变速
它要让天地知道
让世界看见
什么是真正的大巴山
人常说弹指一挥间
其实说的就是三五年
2005年至2008年
任河举起了一座电站
最大坝高155米 总蓄水库容3.154亿立方米
平均发电量4.498亿千瓦时
还是全国首座折线型面板堆石坝哩
新世纪用了四年的时间
将一座大巴山开天辟地的高坝水库
将一座长江三峡也似的高峡平湖
矗立在世人的眼前
(当然也是相形见绌的老房子面前)
石破了 天惊了
星移了 斗转了
七百里大巴山开了天眼
悬崖峭壁猝不及防
山地林水乱了方寸
冉家坝傻眼了
老房子傻眼了
这变化来得这样陡
这机遇来得太突然
一盘经年历月慢吞吞的棋
加快节奏 落子不悔
重新洗牌
重新布局
重新谋算
重新投子
重新运作
重新复盘
老房子对面的火烧坡
那个陡啊
猿猴攀不住
水土挂不住
房舍立不住
一个木盆没搁稳
呯呯嘭嘭滚下河
那才是穷得舔灰了
那才是贫得彻底了
谁想到峡谷深底的河水
会拱天拱地的涨上来呢
谁想到寸草不生的孤坡寡岩
还会丈量着变成钱呢
千年的岩地交给水
百年的老屋交给水
下山了 上街了
建新家了 创新业了
人往低处挪
怎么天地还反倒宽起来?
老房子面前的河滩地
进入坝前了
任河款款的臂弯里
怎么变得这样温暖
河床干了水
坡地砌了坎
楼房排了队
街道镶了边
第一条街就叫“一条街”
第二条街就叫“二条街”
第三条街就叫“三条街”……
农民取名真简单啊
眼下虽只有八九条
往后呢
那不要叫百条街千条街?
条条街道通大坝
大坝那个高啊那个宽啊那个牢实啊
祖祖辈辈谁见过
库水那个满啊那个深啊那个绿啊
水还可以堆得这样厚
库区的人家搬迁了
溯流而上搬进了县城
顺流而下搬到了坝区
沿河的荒坡不见了
水滋润着 水养护着
看上去抹得一展平
高山的林树降下来了
高山的草花降下来了
却原来这么多年
你藏在深闺 只向蓝天袒开心扉
只向白云露出笑靥
终于一只亮的杯
在大巴山南麓
半高半低地举起
一面明的镜
照见触底的天 流走的云
倒的山 浮的树
抖的音 漂的影
巴山人多年干涸的梦想
要浸湿 要滋润
要鼓荡 要充盈
老房子早已按捺不住
冉家坝早已按捺不住
坝区和库区早已按捺不住
不是蠢蠢欲动
而是应运而生
啥都差就是不差劳动力
一辈一辈攒下的原始的劲头
鼓鼓的 昂昂的 嗷嗷的
早就等一个突破口
早就等一个什么契机来点燃
空前规模的水电工程
大山深处的男女老少父老乡亲
一个个全都摇醒了
一家家全都摇活了
筑大坝啊开隧洞啊修公路啊建房屋啊
锯木料啊凿石料啊拉材料啊抬机器啊
养猪羊啊辟菜园啊种果树啊植草坪啊
要的是人力要的是人才
要的是计谋要的是智慧
各找门路吧
各得其所吧
各尽所能吧
各显神通吧
老房子冉家这下神气了
好歹算是个近水楼台
好歹多读了几句书
好歹脑瓜儿转得快
好歹关系走得熟
有的干上了力气活
有的才不满足于力气活呢
有人混上了电站技术员
有人当上了运输队长
有人当上了包工头
有人干上了供货商
有人开公司
有人开门市
有人开旅社
有人开饭馆
有人兴果园
最差也是个炊事员嘛
淘着电站的米 煮着车间的饭
炒着工地的菜
肉儿油儿酒儿田米儿
那个史无前例浓浓的香啊
第七章 春临大地乍暖还寒
这天 老房子那位老二辈
年龄最长的冉幺爷
照例一手杵着长烟杆
一手捻着两枚“佛珠”
走进院坝
细细看那棵石榴树
树老了 叶落了
树干皱了 佝偻了
百年老树了
坚持着隔年挂一次果
这都已经不错了
你我都等到了今天
尝到了酸酸甜甜的果实
说不定还要绽新芽哩
这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
手里的“佛珠”就这么捻着 响着
老房子老老小小心里明白
幺爷那不是什么佛珠
而是两枚发黄的银元
那是幺爷的大伯传给他的
那可是幺爷的宝贝疙瘩
那里边还有个故事哩
听说那是“老解放”的时候
有一天冉家坝来了一支队伍
都说是“官如洪水兵比猛兽”呢
老百姓都躲进了深山
冉大伯走得匆忙
一坨用笋壳包着的盐巴还绑在屋梁上
咳 怎么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忘了呢
过了几天 大兵撤走了
大伯急奔回屋一看
那坨盐巴还绑在那里
桌上搁了两枚银元 一张纸条
请来村里唯一识字的补锅匠看看
纸条上写着——
“老乡 我们是红军
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
屋里的盐巴我们没动
这两块银元
给老乡再去买点盐……”
大伯遇上了天下最好的队伍
大伯就把天下最贵重的银元传给幺爷了
幺爷就知道天下最贵重的是什么东西了
幺爷就把两枚银元捻得油光光的了
后人们就知道银元是幺老辈子的“佛珠”了
常言道大房出长孙 幺房出老爷
寿延高高的冉幺爷
读过私塾的冉幺爷
人老珠未黄
还真算是难得的人才
他爱读个古书爱看个报
很有些字墨
很有些眼光哩
常常口吐莲花 语出惊人
多时髦的一些词儿
竟由他嘴里讲出来
老爷子人年老心年轻得很哪
算是饱经沧桑了
算是看破红尘了
(我看还有一点儿与时俱进呢)
哪朝哪代
有这样幸运顺畅之事呢
老房子家家修起了新房子
后生们个个有了用武之地
田地征了
林山用了
屋基占了
锄头没多大用场了
滚滚而来的红利
什么青苗赔偿费呀
征地补偿款呀
房屋拆迁款呀
扶贫专项款呀
农业开发款呀
社会救助款呀
创业补助款呀
社保医保报销金呀
贫困助学金呀
政策太好 农民得实惠
从未想过的大票子
从未见过的大票子
天文数字的大票子
不敢置信的大票子
打到折子上怀里揣着
农民还跟城里一样可以领工资了
占地移民交齐养老保险
男60岁 女55岁
退休就拿定月养老金了
(那工资还年年看涨哩)
穿草鞋的老房子
一不留神就穿上皮鞋
从乡村跨进城镇了
鸟枪换炮啊
糠箩跳米箩啊
这生路这活路这财路挡都挡不住啊
偌大一个电站工程
偌多一批配套工程
不就是一个天大的扶贫项目么
不就是一个聚宝盆么
凭着老辈子给的一双手
从不停闲的一双手
只要你肯干 肯吃苦
肯流汗 肯动脑筋
举手投足都是钱哪
丫丫草草都是钱哪
人人都能有吃有穿
个个都能好住好行
大把大把的整花钱
小把小把的零花钱
这日子真是掉进了蜂糖罐儿
可这些天冉幺爷却呕了气啊
都老人家了
都过气明星了
气啥呢 气啥呢
气老房子那一群死女子
多年的媳妇
多年的妯娌
说老并不老说嫩并不嫩
一个个当上全职太太了
一个个攀比着玩时髦了
你买一件金银首饰
她买一件高档衣服
涂脂抹粉的
穿金戴银的
每天拎着个猪腰子钱包
逛街呀 串门呀 打牌呀 轧金花呀
娃娃不想带
饭都不想煮
耍惯了 玩疯了
百无聊赖晒了些太阳过冬
无所事事歇了些荫凉度夏
家里全甩给男人家
男人家尽是些“耳朵”
外勤内勤全承包
又要做工挣钱
又要做饭带崽
一个个累得直不起腰来
还点头哈腰乐呵呵的
这世道真有点看不懂了
这是在深山呀
这是在僻壤呀
往年往月妇女没地位
吃饭都不能上桌呢
那些年日子清苦
夫妻都是勤刨苦做
没日没夜地一起苦干
眼下怎么啦
妇女占了半边天
(看这样子还要占整天呢)
有个媳妇说
老娘往时苦狠了 累狠了 穷狠了
如今就该享点现成福
要把青春夺回来
要把损失补回来
要把岁数赚回来
要把休闲耍回来
此话差矣
此话羞矣
巴山人从来勤劳为本
老房子从来白手起家
日子开始好过了
还有多少难过的人哪
不见后山还有贫困户
吃不上田米儿么
穿不上新衣裳么
街上的高山搬迁户
还没安顿下来哩
还没分清东南西北哩
还没找到发财的路径哩
没了山林 没了土地
一时半会儿心里没了底
还等着政府来安排
还等着有人来指拨哩
你们这没日没夜地耍
没完没了地闲逛
耍的是钱哪
逛的是命哪
“坐吃山空”懂不懂啊
(何况你那“山”还只是个土堆堆呢)
谁人看着不叹气呀
谁人看着不痛惜呀
久饿之人暴饮暴食
会把小命儿贴进去的
冉幺爷笃着长烟杆说
不知好歹的背时女娃子些
有福你们都享不来福
生就一副受穷的相
是啊 老房子的
姑嫂姐妹老少爷们
你们可否作好了准备
除了财富的积累资金的储备
还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呢
还要有文化的补充呢
还要有内涵的养成呢
吃惯了黄连 初尝蜜糖
犹如春临大地乍暖还寒哪
还得披上刚刚脱下的衣衫
千百年一块叫做贫穷的纹身
连皮带肉铲下来疼不疼呢
祖祖辈辈的紧日子
一旦松了
散马无笼头的
看你怎样能收放自如
营养不良的大巴山
面黄肌瘦的大巴山
现在开始着肉了
有血色了
身强力壮了
脱胎换骨了
小小老房子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证明
看似猝不及防之间
你接受了么
你适应了么
你清醒了么
你计划了么
你精打细算了么
你细水长流了么
你勤俭持家了么
你瞻前顾后了么
一句话——你富得起么
老房子呀
没人教你哩 没人理你哩
你自问自答 自说自做吧
第八章 贫困农户来了亲人
这边冉幺爷气归气
那边扶贫的队伍进了村
人民政府派人来
住进了低山
住进了高山
高山农民大都搬下了河
靠着场镇 靠着河坝 靠着公路 靠着电站
尽其所长 安排找门路
连外出打工的也回来了
家乡就地觅财路
胜过他乡下蛮力
离乡背井除了锅巴没有饭哪
现在知道挨着家乡有搞头了
现在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
祖辈传下的绿水青山
却原来就是金山银山哪
多亏了这些扶贫干部
多亏了这些指点迷津的手
全区几千户
乡村万多人
多远的住家多远的路
多宽的范围多陡的坡
驻村干部才不管哩
才不怕哩
瞅着那冒炊烟的去处
一处一处去走访
一家一户去建档
一人一人去规划
一步一步去落实
后山有家窎远户
都是冉家人哪
都是自家人哪
夫妇双腿都有残疾
秋冬四季身上只是遮块烂布
家无隔夜粮
老鼠都不愿来登门
当年十片圆萝卜
包在红纸里
权当面饼送人情
人说穷得四壁空空
他家四壁都没有呀
有的是直射里屋的烈日
有的是对穿对过的寒风
低人一等度时光啊
走不下山
不能走下山
男人打得一手好草鞋
女人绣得一手好鞋垫
乡里的书记上来了
乡里的书记又上来了
乡里的书记再上来了
书记也姓冉
冉冉相望
止不住珠泪冉冉哪
冉书记说他上来晚了
冉书记说他上来少了
工作没做好
对不起冉家这个小家族
对不起中华这个大家族
政府在街上建了高山移民安置房
冉家夫妇分了一套
铺笼罩被锅碗瓢盆都备齐
打草鞋的木马绣鞋垫的草墩
只等主人来入住
两副滑竿 八个壮汉
护着扶着抬下山
闪闪悠悠抬下山
下来了 进新家了
不走了 不不还要走啊
如舟的草鞋落了地
如花的鞋垫贴了脚
坐地行千里
手上弄乾坤
土色土香的好鞋好垫
描龙绣凤销四方
两对好胳膊
搭伴周围无数的好腿
健步如飞走天涯
地势好了 生活惯了
也有不愿下山的哩
海拔1800米的方斗坪
也来了个一脚踏三省
陕南的花骨朵伸过来
川东北的蜜蜂探过来
在渝东北的野村里幽会哩
一条掩脚背的方斗河
玻璃一样在沟里静静搁着
水里是斑驳的鹅卵石
河上是整木的树干桥
两岸是难得的河谷沃土
再两边是不难得的连绵林山
石瓦盖顶的石房
石块砌墙的石房
看来实心实意要长住下去了
垛木垒就的牛羊圈
哞哞咩咩的叫得山林更幽静
冬天便是齐膝的大雪
看上去银装素裹 分外妖娆
可屋里灰坑柴火那个烤啊
考糊了膝盖冻裂了脚跟
老天赐予的一只方斗
长年累月却无粮可装
好风好景不饱肚啊
中看中玩却不中用
山民为填饱肚子世代奔波
跑瘦了岁月
枉费了韶光
扶贫干部上来了
挨家挨户聊起了家常
一家家游说呀
一个个劝呀
一笔笔账掰着指头算呀
方斗坪好大的一个斗哇
为啥祖祖辈辈都装不满呢
高山风寒 高山土冷
下山吧 下山吧
高山移民 整体搬迁
人民政府在山下修了新城
仿古的街楼 仿古的石桥
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只等主人家前去入住了
能打工的打工
能开店的开店
老年人就啥也别干赋闲晒太阳吧
别看这山间小城眼下冷清点
往后游人胃口吊高了
可是专挑人迹罕到的世外桃园哩
旅游一发展
人气一起来
那可是一发不收千金难买啊
行啊 行啊
扶贫干部嘴皮都磨破了
工作同志脚板都跑大了
都是为我们好啊
人民政府啥都想到了
人民政府安排周到了
八抬大轿都到屋了
偌大方斗里的“新媳妇”
还在磨蹭什么呢
快上轿 快上轿
可这位又是姓冉的冉大爷
他说他要留下来
儿孙下山创新业
他在山上守旧摊
工作同志不是说
方斗坪这“金饭碗”要端起来么
他舍不得饲养的一群牛羊啊
牛羊一叫
这山里的野物就不敢出来了
这山里的风水就不会破坏了
山外的游客就可以进来了
我就可以给他们做饭吃了
这山上的农家乐开起来
方斗坪就香起来了
这山村就兴旺起来了
山上山下 互通有无
新居老屋 前呼后应
一来二往
山上山下都搞活泛了
扶贫干部说的旅游旅游
我当是个啥新鲜玩艺呢
就是我到你家门口去玩
你到我家门口来玩
屋里的饮食弄到坡上去吃
坡上的饮食弄到屋里去吃
打伙都玩个高兴
打伙都吃个新鲜
舒服日子就这样来到了
老人家不幸言中了
如果是树呢 挪一挪可不得了
如果是人呢 挪一挪就活了
半挪不挪的就活了
山下场镇成了旅游地
山上方斗成了旅游村
冉家坝的游客
县城的游客
重庆的游客
安康的游客
万源的游客
开起小车进山来
坐起大车进山来
邀邀约约进山来
牵起线线进山来
原汁原味的小桥流水
土色土香的石瓦石墙
吹吹打打的锣鼓唢呐
清脆悦耳的山歌谣曲
满坡满垄的蒿草葵花
满河满滩的虾蟹小鱼
暖手暖脚的灰坑柴火
油香扑鼻的腊肉香肠
热气腾腾的红苕洋芋
炙手可热的天麻党参
藏在深闺
人知了 人识了
多少来客心已醉
多少游人不思归……
第九章 人说巴山好风光
一只罗盘
校出了巴山的方位
一只宝盆
聚拢了四方的财富
一面明镜
照出了周遭的风景
一只天眼
看见了夜空的黎明
这真是一水成库百媚生
一站生电放光明哪
巴山水库成了“巴山湖”
标进了县里的旅游地图
画家过来支画板
摄影家过来对镜头
作家过来抒豪情
钓鱼竿伸来打比赛
摩托艇开来打比赛
旅游团这里那里的小红旗
在山光水色间争艳丽
有人评价眼前的风景说
就像画的一样美
有人评价画家的画说
就像真的一样美
这可把巴山人弄糊涂了
到底是画的比真的美
还是真的比画的美?
一条条公路过来了
一座座桥梁出现了
一道道隧洞贯穿了
沿湖的路 盘山的路
出县的路 出省的路
过河的桥 过街的桥
走人的桥 跑车的桥
过人的洞 过车的洞
过水的洞 过电的洞
远远近近里里外外的“电影气气”
弥漫在巴山的空气里
机械的气息 搏动的气息
新鲜的气息 希望的气息
给暮气沉沉的巴山带来几多惊喜
水库大梁上建起了机场
直升机趁着起落瞄一眼水库的秀色
高速路也在修建了
2022年要经过水库哩
渝西高铁列入了前期规划
也要和水库擦身而过
也要和冉家坝擦身而过
(当然也要和老房子擦身而过啰)
老房子却有些茕茕孓立
房拆了 人散了
只有居中的一栋立着
只有院坝的石榴树立着
四壁土墙 残檐乱瓦
一截躯干 临风瑟索
你是想做一个标本么
你是想存一段历史么
你是想留一点记忆么
你是想造一种反差么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陈氏家族长在这块屋基里
巴山农民生在这块土地上
这辈子我就活在这里了
这辈子我就定在这里了
走了还要回
走也走不远
这儿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
这儿如今是金山银山
这儿如今是大道通天
这儿如今是丰衣足食
这儿如今是幸福家园
云开了 天开了
山明了 水透了
满世界都敞敞亮亮的了
照见一个叫做“小康”的神灵
在秦巴山区的土地上
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
一亩三分 一亩三分 一亩三分……
无所不在地游荡
不留缝隙地游荡
决战决胜地游荡
全面凯歌地游荡
2020年1月初稿 2月修改
作者情况:向求纬, 男, 73岁,重庆市万州区人。196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大巴山区城口县待了20年(插队落户13年,工作7年),1985年调入万县日报(现三峡都市报)作主任编辑。已退休。
1966年开始在全国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以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见长,已写作、发表文学作品600多万字,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级获奖,作品曾被收入国内各种选集。曾主编10多套文学丛书,出版长篇叙事诗集《喊峡谣》、《老乡何其芳》,诗集《巴山情》、《三峡吟》、《三峡恋》、《搂定三峡》、《求纬朗诵诗》,散文集《远山的呼唤》、长篇散文集《巴山老知青》,报告文学集《大地不了情》、《三峡的脚步》、《永远的绿洲》,尤以2003年出版的以三峡移民为题材的长诗《喊峡谣》、2009年以何其芳为题材的长诗《老乡何其芳》和2014年出版的知青题材长篇散文《巴山老知青》较有影响。《巴山老知青》2017年获第七届重庆文学奖,已被改编为高清同名电影。现为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
通 讯 处:重庆市万州区三峡都市报社 邮 编:404000
电 话:(023)58139386(宅) 13668469726(手机)
邮 箱:395923883@qq.com
微 信:W13668469726
身份证号:512201194611030813
(叙事诗) 向求纬
谨以此诗,献给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巴山区父老乡亲
——题记
第一章 大巴山腰间的一个胎记
老房子在山上
大巴山南麓之一隅
当初川陕两省交界处
后来渝川陕三省交界处
离陕西近
五六十里就跨过界梁
离四川更近
二三十里就赶钟亭的乡场
可离县城远啊
130里路还隔着一条大河三座大山
老房子在山下
群山环绕的一个低凹处
由东向西倒流的任河
远远地流来
快出县境也就是快出省境了
在这儿拐了个大弯
把这座老房子和老房子们
挽在怀里慢慢地诳
久久地哄
白日夜晚
千年百载
不知睡着没有
不知睡醒没有
大巴山长在腰间藏着掖着的一个胎记
老天朝下看看得见它
世人四处看看不见它
城市走瘸了腿好久也走不近它
那个叫做“现代文明”的娃娃
投错了胎也一时半会投不进这里来
老房子其实很富有啊
四周那山 那岩 那林 那草
面前这土 这地 这河 这水
随便薅上一把都能冒油
都能变金 变银
本来就在福窝窝里躺着哩
抓一把风来轻轻一吹
也能像孙猴子一样要啥变啥
可这块土地却穷得舔灰呀
穷得鬼都不愿生蛋
成年累月 风雨飘摇
子子孙孙 没完没了
重复着一副似曾相识的情景——
超生的娃娃们蜷曲在灰坑旁
一群不辨眉眼的灰老鼠
掏着抢着剥着烧熟的种洋芋
一个个吃得口水滴嗒的
大人们藏在成堆的包谷壳里
赤身露体
(报上曾有过“牛吃‘铺盖’”的说法)
一家一条公用的“油渣裤”
谁出门谁穿
老人们躺在无药可医的篾巴折床上
听着天由着命
病病哀哀地成天发愁
地里是朝天一把籽坐地等花开
小包谷挨着地长成“野鸡啄”
麻洋芋不等成熟就被“阉割”提前当口粮
红苕只长藤叶根须儿却不结大疙瘩
无油无盐的日子
油就免了 最要命的是缺盐呀
上了点年纪的巴山人
脖颈上多半吊着一只大瘿包
一把羊角锄
起呀落呀挖呀掘呀
水流了 山秃了
土瘦了 人老了
做也做了 干也干了
苦也苦了 累也累了
何时能饱腹
何时能蔽体
何时是个头?
贫困埋的根
贫困惹的祸
贫困遭的罪
贫困作的孽
历史留下的一层皮
到底能不能蜕下来?
根深蒂固的一位“阿斗”
到底能不能扶起来?
第二章 老房子蹲在三省交界处
老房子是一群房子
茅草盖顶 石瓦盖顶
黄泥筑墙 石块砌墙
整体坐北朝南
个体却杂乱无章
有房子必有一孔猪圈
秸秆垛木 天穿地漏
雨天钻个人进来解便
背湿得很哪
包谷壳还老是揩不干净
老房子是一群人
二三十家 百十口子
当家人统统姓冉
(要不然面前的场镇怎么叫冉家坝呢)
都说“冉家坝的布染不得”
老房子真没人惹得起哟
同胞兄弟 隔房姐妹
同天同地 同天异地
地坝边上一棵石榴树
年年结金果
岁岁抱成团
你锅里有我碗里有
你抱肚子饿我也不饱腹
同宗的血脉祖传的豪气
吃一起 住一起
穷一起 苦一起
倘能富呢
是不是也能在一起
没听说贫困与海拔有关
三位数的海拔
老房子却比四位数幸运
好在近处有一些坡地
好在远处有一些荒地
任河那低低的臂弯里
一条猪屎河流过去
一条猪屎街算是场镇了
这样老房子就算是近郊了
靠着河靠着街是最大的优势
关键还有一点水田
稻谷刚好够交公粮
够帮助国家吃上一口田米(大米)了
够帮助公家人吃上一顿田米了
够自家过年的时候尝尝米饭味道了
(那可是大人细娃盼星星盼月亮的团年饭哪
连刨七口才睁眼睛呢)
这可比四周高山农家强多了
没听说“高山老二下不得河
下河就是棕包脚
烤的是转转火
吃的是洋芋果
喝酒吃肉好家伙
栽秧搭谷奈不何
要想吃一颗田米儿
转世投胎重来过”
老房子个个人勤快啊
男人种地 女人摘茶
纵是苦日子也算计着过
出门风都要抓一把
走路也要采一兜猪草
清晨打早工开荒地
回来带回一捆柴
肚子都还咕咕叫呢
猪头牲口就打圈了
紧赶着又要出门上工
搅一顿包谷糊糊将就喝了
生产队站成“翼口”(干活的队列)挖地
歇气了
妇女抓起奶子朝后一甩
背上的娃娃就捉住进食了
要不然将娃娃搁在茶树蔸下
让他和蚂蚁蚯蚓玩耍
有时还有一条小蛇儿光顾
娃娃从不知道啥叫害怕
这大巴山就用羊角锄这么挖着
这任河水就让奶娃娃这么背着
通向山外的小路就让几个背二哥走着
陕南的风 川东北的风
途经此地赶紧一抹而过
忙早忙晚 累死累活
包谷面糊都喝不饱啊
春荒时节还得打蕨根哩
老房子的土墙石瓦
盖着蹲着有些不安生了
这哪儿是个事啊
坐牢房还有个期限呢
(还别说真有个孤儿
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想去坐牢
去住不要钱的房吃不要钱的饭)
这铁桶一般的大山
这可怜的一亩三分田地
这林海树海花海草海包裹的苦海
何时才能触底反弹
何时才能靠边登岸
后来山林田地分下了户
这日子就缓过一口气来
再不在生产队排队干活
出工就指望太阳落
锄把老杵着都长了老木菌了
劳动力多 劳动果实少
浑身的劲儿没使出
一身的疙瘩肉没结出疙瘩
这人哪 真是贱相
大锅饭吃着老吃不饱啊
小锅小灶喝面糊也觉着香
春耕时节——
犁田了 打耙了
你借我的牛
我借你的耙
小小稻田像经佑幺儿
一遍遍耱得个油光水滑
栽秧了 播种了
一群群一家家换工了
嫩胡豆下着栽秧酒
山歌唱得呵吙连天地响
秋收时节——
你家扛来大拌桶
他家背来大背篼
嚓嚓嚓嚓割呀割呀
嘭咚嘭咚搭呀搭呀
散开的谷把子放倒在地
合拢的谷把子一飞冲天
这单干才有劲哟
这合作才有力哟
山林田地承包50年不变
半个世纪的收成
看似不多年年有
一瓢一勺不流外人田
咱祖辈的农民图个啥呢
地里有刨的
锅里有煮的
身上有穿的
膝下有逗的
一日两餐不断顿
(农家开饭是二五八)
就够了 就足了
不盼了 不想了
第三章 “大背老二”带来了“电影气气”
远近闻名的冉氏宗族
老一辈一个个撒手而去
在老房子背后的楠竹林里躺着
让后阳沟共用的一眼泉水
滴着冬冷夏凉的泪
老二辈也老了
白头巾青布衫裹着
铜头长烟杆杵着
走来走去 磕来磕去
后生们也不大搭理了
“变了泥鳅就得钻土”呀
“头上蒙块布把着活路做”呀
这祖训听着也有些腻了烦了
老三辈们正当年呢
精力旺盛 想入非非
这日子不能这样过下去了
走出去 跑出去
看看山外啥模样
听听山外啥响声
听说这地球大得很哩
难不成都跟这山里一样光景
年轻人正这样想着
驻村干部来了
都是些书记呀社长呀武装部长呀委员呀
每人包干一两个村
都是庄稼人出身
本乡本土的
干工作做事情没挑剔的
喝酒吃肉也很在行
酒杯一端
就有些云天雾地的了
就有些口无遮拦了
老房子尽是些机灵鬼哟
日子再紧
这穿肠过的东西随时攒着
(老房子就是驻村干部的伙食团呢)
地坝里摆上酒壶土碗
几块洋芋片几颗炒黄豆就可佐酒
实在不行就烟下酒酒下酒龙门阵下酒
肚里一发烧
舌头就不灵活了
话匣子就打开了
想挣点油盐钱么
想甩脱穷皮皮么
年轻人是得往外跑哩
这石骨子坡坡肯定挖不出金娃娃来
山外的月亮比这儿都大
山外的票子比这儿都长
还有山外的女娃子
嘻嘻,比这儿都……
不过话又说回来
找出路 先修路
一步路都走不伸展
天大的想法有什么用
地大的本事有什么用
县里有计划
专区有计划
省里有计划
国家有计划
这冉家坝要修公路了
本县的大山
怕是世袭的骨头太硬吧
这路要从外省绕道来……
出门要修路
挣钱先修路
铁桶般的大山严丝合缝
咱要让它裂开一条缝
破开一道口
让鲜活的空气透进来
让折射的阳光探进来
让新奇的图景映进来
让崭新的希望照进来
论修路
老房子有的是劳力
老房子有的是内行
陈氏宗族的活先人发一声喊
山山岭岭都回应
公家来修路
私人打帮手还不行么
有人出人
有力出力
有物出物
个别有钱的还得出钱哩
规划线路上有个垮石湾
坚硬的岩石一点不垮
拦路虎呀 老大难呀
工程技术人员着了急
别慌
老房子有个高中生
平日里喜好摆弄点机械呀雷管磺药什么的
自学成才的能工巧匠
这小子来到垮石湾
和技术员厮守在一起
山梁上比划
图纸上勾描
跑县里蹲图书馆
去水电局请教技师
这一天来了个人员大撤离
放上警戒望上风
就在这千年沉闷的僻静处
震天动地一阵炮响
定向爆破成功了
垮石湾名副其实了
这老房子的回乡青年
还真有点接生婆戴眼镜——
看你娃娃不出来!
说话之间好快呀
路来了 路通了
川陕交界处来了个弯弯绕
跨县跨市跨省地过来了
不大宽的路
不大平的路
(可那是盘古开天地的路啊)
通车典礼的横幅挂出来了
十余辆汽车披红挂绿
鼓着眼睛 喘着粗气
挪过来了 挪过来了
山上的老农下来了
祖传的小脚 过年的新衣
扶着搀着下来了
界梁那边的老农过来了
背着干粮 备着火把
也想来沾一点喜气呢
谁见过这样的“大背老二”呢
不喝酒 不吃粮
拉货几吨十几吨
这得俯下身子看个仔细才行
这家伙到底是公是母?
老房子有个电影放映员
天天柴油机一响竖起大银幕
这会儿煞有介事了:
大家闻闻大家闻闻
这大背老二好大一股电影气气!
这电影气气扩散的地方
喇叭一响 黄金万两
大巴山一隅的第一条公路
窄是窄点
弯是弯点
糙是糙点
绕是绕点
(进县城还得出省界呢)
可打通了血脉连上了筋
自个儿心爱的就是宝啊
走人户呀 串亲戚呀
背力呀 搭车呀
跑车呀 运货呀
就开个手扶拖拉机也神气啊
突突突突像个土皇帝
人不熟悉也不得刹一脚哩
还有闲人也出门瞎逛逛了
顺着公路 指点江山
(这怕是后来“旅游”的前身?)
是呀 是呀
这就近的景点这么多
眼皮子下的风景这么美
往时为啥就看不见呢
为啥就走不拢去呢
谁说灯下黑呀
这桐油灯马灯煤油灯电灯底下
那可是多乖多亮堂呢
第四章 任河拐了一个几字弯
面前就是一条河
那可不是大巴山第一条河
自东向西倒流三千八百里
千年百年地流来
悄没声息地流来
流进汉水 注入长江
流得大巴山多年未见异常
流得冉家坝多年未见异常
流得老房子多年未见异常
只是灌了点好田地哟
河水挑来
干涸的土地好歹止一下渴
没力气开渠筑堰啊
天干时节
为争一口沟水
亲兄弟也打得头破血流
只在河里打了些好鱼哟
夏夜
鱼鳖们趴在沙滩上乘凉
提个马灯
一个一个只管往篓子里捡
秋晨
拎一部电话机来到河边
两股电线丢进水里
一阵猛摇
无鳞的鱼儿禁不住电话骚扰
晕头转向窜上来
钻进长竹竿的网兜里
趁着没人的时候
一坨炸药丢下河
鱼儿散浮一片
饱了口福
许多楞小子却成了永远的“一把手”
两三层楼深的绿荫潭里
憋着气钻下去摸鱼
上呀 下呀
钻呀 摸呀
一把鼻血染了绿水
一条大鲢鱼换了些零用钱
这河里的娃娃鱼可惹不起
那是送子娘娘设下的诱饵呢
捉了那鱼会断子绝孙的
可街上的脱产干部才不管那么多哟
炖一罐鱼汤美滋滋地喝
咳 不吃白不吃
山民也要顾嘴巴了
哪管下一代断后不断后
只在河里放了些好木柴哟
峭壁上树棒扔下河
牛麻藤 做绳索
翘紧了 打成捆
一根泡桐树做托柴
掀进河里漂下来
漂到回湾处
正好 捞上来
分成小捆
一趟一趟扛回家
坝里的土瘦了
山上的树光了
河里的鱼少了
老房子的炊烟
冉家坝的炊烟
四山的炊烟
你又能维持得多久
靠山越靠山越空
靠水越靠水越枯
光阴不再
山水不言
老家的山你难道真的不怜人
故乡的水你难道真的不动心
第五章 山外的月亮大又圆
说去说来
还是老房子的年轻人脑瓜儿灵光
多读了几天书
成天想精想怪地想
先是在院坝里牵一根线线
弄来个木匣子挂着
咿咿呀呀地唱起了秦腔
这可稀罕得很哪
后山下来的老农
叼着烟杆转来转去地看
这个把戏了不得呀
那么小个箱箱儿
哪儿装得下那么多人
一个个还嘶声瓦气地唱 唱
后来老房子又弄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叽哩哇啦地说呀 叫呀
这东西就更神奇了
拿在手里的一块“砖头”
连绳索都不牵一根
它还有精神叫?
还有精神嚎?
老房子可不管那么多
只管打自己的主意
这路也通了
信息也来了
年轻人哪还待得住啊
一颗心早飞出了家门
飞出了山门
飞到东南沿海去了
听说那边海风那个呼啸呀
海潮那个汹涌呀
到处想见个山包包都难哩
哪来这么多的大山
那儿的土地又平又宽
哪像我们这边
巴掌宽个地势都叫做“坪”
簸箕大块平地都叫做“坝”
出门去 出门去
出山去 出山去
见一片世面挣几个钱
回来孝敬父母
回来娶个媳妇
回来砌个新房
回来置办家产
冉老三的幺儿邀上几个人
去了东莞一家玩具厂
从小都没玩过玩具
如今玩具堆成山
那个新鲜呀
那个快活呀
这活路比挖地可轻松一半呢
这活路比挖地可划算一倍哩
没过几年
冉老幺炒了那老板
自己牵头造玩具
叫来老房子七大姑八大哥
开了个家族玩具厂
我玩大玩具
你玩小玩具
他玩玩具小部件
几玩几不玩
咦,不愧是老房子出来的灵醒人
腰包多少都鼓了起来
腰杆多少都粗了起来
过个年呀回个家呀
都学着光起宗来耀起祖来
哼 一样的包谷米吃着长大
他老房子凭啥就能发财
新房子旧房子高房子矮房子草房子木房子
都是人 都长手
都出去 都打工
谁都能混出个人样来
这一下悬崖裂了口
洪水开了堤
大巴山拥出了打工仔
四面八方 排山倒海
那个贪婪劲
那个勤劳劲
那个拼命劲
那个聪明劲
要个人来赶哪要个人来赶
可十根手指扯不齐呀
一胞鸡崽不是个个都会叫哩
本以为山外遍地是黄金
却原来条条蛇儿都咬人
冉老七的大儿邀了几个人去灵宝
听说那儿沙里能淘金
捏一把满手都淌金水哩
谁料到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苦功花不开
金沙才不认偷懒鬼呢
沙里淘金 你得用力淘呀
你得流汗水呀
没法子 心生一计
拦在半路上 抢他两个金老板
完事跑进大巴山
找一处老房子躲起来
冉幺爷为这事可是动了气啊
没见你这么打工的
没见你这么挣钱的
不成器的东西
咱冉家怎么养出了这种货色
国法未动家法动
来来来
罚你在神龛前跪三天
水米不沾牙
无令不起身
看你还当不当棒老二
看你做人还像不像人
江河毕竟东流去
节令到了挡都挡不住啊
远处能打工 近处也招工
县里砖瓦厂
区里供销社
乡里加工厂
老房子当仁不让啊
有指标就去
有空子就钻
有活路就做
谁会跟挣钱过不去呢
可挣钱也得有准备啊
挣钱也得有资格呢
初踏脱贫路
还真是五花八门丑态百出
生产队工分记惯了
如今拿工资
诚惶诚恐 藏着捏着
生怕别人看见了
还有人花都不会花
数都不会数哩
冉老九家的三女子
模样长得好
就是读书不用功
好容易跨进学校门
上了些“瞌睡课”
读了些“滑水书”
混了个初中二年级
斗大的字还写不出几个
这次招进了食品站
社员要杀猪
要开屠宰证
冉三妹你给开开吧
堂堂中学生呢
开完拿过来一看
天哪
屠宰种类一栏里
赫然填上社员老爹的名字
这可把社员惹毛了
宰你个老房子亲爹爹哟
你老房子个个都是猪!
一场祸惹得可不小
唇枪舌战 恶语相向
差点儿还动了干戈
说起来令人可叹哪
祖祖辈辈穷惯了
没文化真是不行啊
送去读书吧
送去读书吧
女娃娃多半没这资格
男娃娃都是些二杆子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混几年 混几年吧
认得到钱 认得到秤
能写自己名字就行了
就这还有人不达标呢
那年陕西过来个生意客
一叠崭新的袜子商标
就“买”走了这边的一口袋天麻
还有人用嵌磁铁的秤
称走了成捆的茶叶
难怪学校老师都笑说
别看老房子那些小子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啊
此言过了
此言差矣
老房子算是周遭的佼佼者呢
你看四周老山上
常有些呆儿傻儿下来
见人流着涎水瘮人地笑
满街追打花衣服
满身污垢 衣不蔽体
让人看着好心酸
可眼下路开了 山开了
天开了 云开了
一苗露水一苗草
一只老鸹一片滩
人生在世都有道理
人活着都有他的生路呀
吃饱饭的机会
穿新衣的机会
余钱剩米的机会
过好日子的机会
只要活着眨眼的 喘气的
纵是在这两省交界处
在这冷僻窎远处
在这贫困潦倒处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啊
第六章 一颗明珠落深山
还得说这一条古老的任河
巴山人再老也老不过它
它流赢了 流老了 流走了
那它转个弯干啥呢
直端端流过该多好
它有心啊 有意啊
千百年来的心思
它不说
它不折腾
它让你去猜 去想
连老房子都弄不明白
它隔着一道山梁
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干什么
天看着知道
树围着知道
岩立着知道
风擦着知道
那河水要有大动作
那河水不愿平躺着
那河水出乡出县出省的时候
不会白白地就这么走掉
说时迟 那时快
有朝一日
这河水来了个急刹车
这河水忽然间腾身而起
这河水在山梁间冲开了个洞
这河水再不走弯路了
再不静默无声了
它要对对直直地出乡 出县 出省
它不满足于浇几块田地养几根山柴喂几条鱼儿了
它要如电光石火
如霹雳雷电
如雨露甘霖
如大道通衢
它要变身 变脸 变形 变色 变速
它要让天地知道
让世界看见
什么是真正的大巴山
人常说弹指一挥间
其实说的就是三五年
2005年至2008年
任河举起了一座电站
最大坝高155米 总蓄水库容3.154亿立方米
平均发电量4.498亿千瓦时
还是全国首座折线型面板堆石坝哩
新世纪用了四年的时间
将一座大巴山开天辟地的高坝水库
将一座长江三峡也似的高峡平湖
矗立在世人的眼前
(当然也是相形见绌的老房子面前)
石破了 天惊了
星移了 斗转了
七百里大巴山开了天眼
悬崖峭壁猝不及防
山地林水乱了方寸
冉家坝傻眼了
老房子傻眼了
这变化来得这样陡
这机遇来得太突然
一盘经年历月慢吞吞的棋
加快节奏 落子不悔
重新洗牌
重新布局
重新谋算
重新投子
重新运作
重新复盘
老房子对面的火烧坡
那个陡啊
猿猴攀不住
水土挂不住
房舍立不住
一个木盆没搁稳
呯呯嘭嘭滚下河
那才是穷得舔灰了
那才是贫得彻底了
谁想到峡谷深底的河水
会拱天拱地的涨上来呢
谁想到寸草不生的孤坡寡岩
还会丈量着变成钱呢
千年的岩地交给水
百年的老屋交给水
下山了 上街了
建新家了 创新业了
人往低处挪
怎么天地还反倒宽起来?
老房子面前的河滩地
进入坝前了
任河款款的臂弯里
怎么变得这样温暖
河床干了水
坡地砌了坎
楼房排了队
街道镶了边
第一条街就叫“一条街”
第二条街就叫“二条街”
第三条街就叫“三条街”……
农民取名真简单啊
眼下虽只有八九条
往后呢
那不要叫百条街千条街?
条条街道通大坝
大坝那个高啊那个宽啊那个牢实啊
祖祖辈辈谁见过
库水那个满啊那个深啊那个绿啊
水还可以堆得这样厚
库区的人家搬迁了
溯流而上搬进了县城
顺流而下搬到了坝区
沿河的荒坡不见了
水滋润着 水养护着
看上去抹得一展平
高山的林树降下来了
高山的草花降下来了
却原来这么多年
你藏在深闺 只向蓝天袒开心扉
只向白云露出笑靥
终于一只亮的杯
在大巴山南麓
半高半低地举起
一面明的镜
照见触底的天 流走的云
倒的山 浮的树
抖的音 漂的影
巴山人多年干涸的梦想
要浸湿 要滋润
要鼓荡 要充盈
老房子早已按捺不住
冉家坝早已按捺不住
坝区和库区早已按捺不住
不是蠢蠢欲动
而是应运而生
啥都差就是不差劳动力
一辈一辈攒下的原始的劲头
鼓鼓的 昂昂的 嗷嗷的
早就等一个突破口
早就等一个什么契机来点燃
空前规模的水电工程
大山深处的男女老少父老乡亲
一个个全都摇醒了
一家家全都摇活了
筑大坝啊开隧洞啊修公路啊建房屋啊
锯木料啊凿石料啊拉材料啊抬机器啊
养猪羊啊辟菜园啊种果树啊植草坪啊
要的是人力要的是人才
要的是计谋要的是智慧
各找门路吧
各得其所吧
各尽所能吧
各显神通吧
老房子冉家这下神气了
好歹算是个近水楼台
好歹多读了几句书
好歹脑瓜儿转得快
好歹关系走得熟
有的干上了力气活
有的才不满足于力气活呢
有人混上了电站技术员
有人当上了运输队长
有人当上了包工头
有人干上了供货商
有人开公司
有人开门市
有人开旅社
有人开饭馆
有人兴果园
最差也是个炊事员嘛
淘着电站的米 煮着车间的饭
炒着工地的菜
肉儿油儿酒儿田米儿
那个史无前例浓浓的香啊
第七章 春临大地乍暖还寒
这天 老房子那位老二辈
年龄最长的冉幺爷
照例一手杵着长烟杆
一手捻着两枚“佛珠”
走进院坝
细细看那棵石榴树
树老了 叶落了
树干皱了 佝偻了
百年老树了
坚持着隔年挂一次果
这都已经不错了
你我都等到了今天
尝到了酸酸甜甜的果实
说不定还要绽新芽哩
这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
手里的“佛珠”就这么捻着 响着
老房子老老小小心里明白
幺爷那不是什么佛珠
而是两枚发黄的银元
那是幺爷的大伯传给他的
那可是幺爷的宝贝疙瘩
那里边还有个故事哩
听说那是“老解放”的时候
有一天冉家坝来了一支队伍
都说是“官如洪水兵比猛兽”呢
老百姓都躲进了深山
冉大伯走得匆忙
一坨用笋壳包着的盐巴还绑在屋梁上
咳 怎么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忘了呢
过了几天 大兵撤走了
大伯急奔回屋一看
那坨盐巴还绑在那里
桌上搁了两枚银元 一张纸条
请来村里唯一识字的补锅匠看看
纸条上写着——
“老乡 我们是红军
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
屋里的盐巴我们没动
这两块银元
给老乡再去买点盐……”
大伯遇上了天下最好的队伍
大伯就把天下最贵重的银元传给幺爷了
幺爷就知道天下最贵重的是什么东西了
幺爷就把两枚银元捻得油光光的了
后人们就知道银元是幺老辈子的“佛珠”了
常言道大房出长孙 幺房出老爷
寿延高高的冉幺爷
读过私塾的冉幺爷
人老珠未黄
还真算是难得的人才
他爱读个古书爱看个报
很有些字墨
很有些眼光哩
常常口吐莲花 语出惊人
多时髦的一些词儿
竟由他嘴里讲出来
老爷子人年老心年轻得很哪
算是饱经沧桑了
算是看破红尘了
(我看还有一点儿与时俱进呢)
哪朝哪代
有这样幸运顺畅之事呢
老房子家家修起了新房子
后生们个个有了用武之地
田地征了
林山用了
屋基占了
锄头没多大用场了
滚滚而来的红利
什么青苗赔偿费呀
征地补偿款呀
房屋拆迁款呀
扶贫专项款呀
农业开发款呀
社会救助款呀
创业补助款呀
社保医保报销金呀
贫困助学金呀
政策太好 农民得实惠
从未想过的大票子
从未见过的大票子
天文数字的大票子
不敢置信的大票子
打到折子上怀里揣着
农民还跟城里一样可以领工资了
占地移民交齐养老保险
男60岁 女55岁
退休就拿定月养老金了
(那工资还年年看涨哩)
穿草鞋的老房子
一不留神就穿上皮鞋
从乡村跨进城镇了
鸟枪换炮啊
糠箩跳米箩啊
这生路这活路这财路挡都挡不住啊
偌大一个电站工程
偌多一批配套工程
不就是一个天大的扶贫项目么
不就是一个聚宝盆么
凭着老辈子给的一双手
从不停闲的一双手
只要你肯干 肯吃苦
肯流汗 肯动脑筋
举手投足都是钱哪
丫丫草草都是钱哪
人人都能有吃有穿
个个都能好住好行
大把大把的整花钱
小把小把的零花钱
这日子真是掉进了蜂糖罐儿
可这些天冉幺爷却呕了气啊
都老人家了
都过气明星了
气啥呢 气啥呢
气老房子那一群死女子
多年的媳妇
多年的妯娌
说老并不老说嫩并不嫩
一个个当上全职太太了
一个个攀比着玩时髦了
你买一件金银首饰
她买一件高档衣服
涂脂抹粉的
穿金戴银的
每天拎着个猪腰子钱包
逛街呀 串门呀 打牌呀 轧金花呀
娃娃不想带
饭都不想煮
耍惯了 玩疯了
百无聊赖晒了些太阳过冬
无所事事歇了些荫凉度夏
家里全甩给男人家
男人家尽是些“耳朵”
外勤内勤全承包
又要做工挣钱
又要做饭带崽
一个个累得直不起腰来
还点头哈腰乐呵呵的
这世道真有点看不懂了
这是在深山呀
这是在僻壤呀
往年往月妇女没地位
吃饭都不能上桌呢
那些年日子清苦
夫妻都是勤刨苦做
没日没夜地一起苦干
眼下怎么啦
妇女占了半边天
(看这样子还要占整天呢)
有个媳妇说
老娘往时苦狠了 累狠了 穷狠了
如今就该享点现成福
要把青春夺回来
要把损失补回来
要把岁数赚回来
要把休闲耍回来
此话差矣
此话羞矣
巴山人从来勤劳为本
老房子从来白手起家
日子开始好过了
还有多少难过的人哪
不见后山还有贫困户
吃不上田米儿么
穿不上新衣裳么
街上的高山搬迁户
还没安顿下来哩
还没分清东南西北哩
还没找到发财的路径哩
没了山林 没了土地
一时半会儿心里没了底
还等着政府来安排
还等着有人来指拨哩
你们这没日没夜地耍
没完没了地闲逛
耍的是钱哪
逛的是命哪
“坐吃山空”懂不懂啊
(何况你那“山”还只是个土堆堆呢)
谁人看着不叹气呀
谁人看着不痛惜呀
久饿之人暴饮暴食
会把小命儿贴进去的
冉幺爷笃着长烟杆说
不知好歹的背时女娃子些
有福你们都享不来福
生就一副受穷的相
是啊 老房子的
姑嫂姐妹老少爷们
你们可否作好了准备
除了财富的积累资金的储备
还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呢
还要有文化的补充呢
还要有内涵的养成呢
吃惯了黄连 初尝蜜糖
犹如春临大地乍暖还寒哪
还得披上刚刚脱下的衣衫
千百年一块叫做贫穷的纹身
连皮带肉铲下来疼不疼呢
祖祖辈辈的紧日子
一旦松了
散马无笼头的
看你怎样能收放自如
营养不良的大巴山
面黄肌瘦的大巴山
现在开始着肉了
有血色了
身强力壮了
脱胎换骨了
小小老房子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证明
看似猝不及防之间
你接受了么
你适应了么
你清醒了么
你计划了么
你精打细算了么
你细水长流了么
你勤俭持家了么
你瞻前顾后了么
一句话——你富得起么
老房子呀
没人教你哩 没人理你哩
你自问自答 自说自做吧
第八章 贫困农户来了亲人
这边冉幺爷气归气
那边扶贫的队伍进了村
人民政府派人来
住进了低山
住进了高山
高山农民大都搬下了河
靠着场镇 靠着河坝 靠着公路 靠着电站
尽其所长 安排找门路
连外出打工的也回来了
家乡就地觅财路
胜过他乡下蛮力
离乡背井除了锅巴没有饭哪
现在知道挨着家乡有搞头了
现在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
祖辈传下的绿水青山
却原来就是金山银山哪
多亏了这些扶贫干部
多亏了这些指点迷津的手
全区几千户
乡村万多人
多远的住家多远的路
多宽的范围多陡的坡
驻村干部才不管哩
才不怕哩
瞅着那冒炊烟的去处
一处一处去走访
一家一户去建档
一人一人去规划
一步一步去落实
后山有家窎远户
都是冉家人哪
都是自家人哪
夫妇双腿都有残疾
秋冬四季身上只是遮块烂布
家无隔夜粮
老鼠都不愿来登门
当年十片圆萝卜
包在红纸里
权当面饼送人情
人说穷得四壁空空
他家四壁都没有呀
有的是直射里屋的烈日
有的是对穿对过的寒风
低人一等度时光啊
走不下山
不能走下山
男人打得一手好草鞋
女人绣得一手好鞋垫
乡里的书记上来了
乡里的书记又上来了
乡里的书记再上来了
书记也姓冉
冉冉相望
止不住珠泪冉冉哪
冉书记说他上来晚了
冉书记说他上来少了
工作没做好
对不起冉家这个小家族
对不起中华这个大家族
政府在街上建了高山移民安置房
冉家夫妇分了一套
铺笼罩被锅碗瓢盆都备齐
打草鞋的木马绣鞋垫的草墩
只等主人来入住
两副滑竿 八个壮汉
护着扶着抬下山
闪闪悠悠抬下山
下来了 进新家了
不走了 不不还要走啊
如舟的草鞋落了地
如花的鞋垫贴了脚
坐地行千里
手上弄乾坤
土色土香的好鞋好垫
描龙绣凤销四方
两对好胳膊
搭伴周围无数的好腿
健步如飞走天涯
地势好了 生活惯了
也有不愿下山的哩
海拔1800米的方斗坪
也来了个一脚踏三省
陕南的花骨朵伸过来
川东北的蜜蜂探过来
在渝东北的野村里幽会哩
一条掩脚背的方斗河
玻璃一样在沟里静静搁着
水里是斑驳的鹅卵石
河上是整木的树干桥
两岸是难得的河谷沃土
再两边是不难得的连绵林山
石瓦盖顶的石房
石块砌墙的石房
看来实心实意要长住下去了
垛木垒就的牛羊圈
哞哞咩咩的叫得山林更幽静
冬天便是齐膝的大雪
看上去银装素裹 分外妖娆
可屋里灰坑柴火那个烤啊
考糊了膝盖冻裂了脚跟
老天赐予的一只方斗
长年累月却无粮可装
好风好景不饱肚啊
中看中玩却不中用
山民为填饱肚子世代奔波
跑瘦了岁月
枉费了韶光
扶贫干部上来了
挨家挨户聊起了家常
一家家游说呀
一个个劝呀
一笔笔账掰着指头算呀
方斗坪好大的一个斗哇
为啥祖祖辈辈都装不满呢
高山风寒 高山土冷
下山吧 下山吧
高山移民 整体搬迁
人民政府在山下修了新城
仿古的街楼 仿古的石桥
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只等主人家前去入住了
能打工的打工
能开店的开店
老年人就啥也别干赋闲晒太阳吧
别看这山间小城眼下冷清点
往后游人胃口吊高了
可是专挑人迹罕到的世外桃园哩
旅游一发展
人气一起来
那可是一发不收千金难买啊
行啊 行啊
扶贫干部嘴皮都磨破了
工作同志脚板都跑大了
都是为我们好啊
人民政府啥都想到了
人民政府安排周到了
八抬大轿都到屋了
偌大方斗里的“新媳妇”
还在磨蹭什么呢
快上轿 快上轿
可这位又是姓冉的冉大爷
他说他要留下来
儿孙下山创新业
他在山上守旧摊
工作同志不是说
方斗坪这“金饭碗”要端起来么
他舍不得饲养的一群牛羊啊
牛羊一叫
这山里的野物就不敢出来了
这山里的风水就不会破坏了
山外的游客就可以进来了
我就可以给他们做饭吃了
这山上的农家乐开起来
方斗坪就香起来了
这山村就兴旺起来了
山上山下 互通有无
新居老屋 前呼后应
一来二往
山上山下都搞活泛了
扶贫干部说的旅游旅游
我当是个啥新鲜玩艺呢
就是我到你家门口去玩
你到我家门口来玩
屋里的饮食弄到坡上去吃
坡上的饮食弄到屋里去吃
打伙都玩个高兴
打伙都吃个新鲜
舒服日子就这样来到了
老人家不幸言中了
如果是树呢 挪一挪可不得了
如果是人呢 挪一挪就活了
半挪不挪的就活了
山下场镇成了旅游地
山上方斗成了旅游村
冉家坝的游客
县城的游客
重庆的游客
安康的游客
万源的游客
开起小车进山来
坐起大车进山来
邀邀约约进山来
牵起线线进山来
原汁原味的小桥流水
土色土香的石瓦石墙
吹吹打打的锣鼓唢呐
清脆悦耳的山歌谣曲
满坡满垄的蒿草葵花
满河满滩的虾蟹小鱼
暖手暖脚的灰坑柴火
油香扑鼻的腊肉香肠
热气腾腾的红苕洋芋
炙手可热的天麻党参
藏在深闺
人知了 人识了
多少来客心已醉
多少游人不思归……
第九章 人说巴山好风光
一只罗盘
校出了巴山的方位
一只宝盆
聚拢了四方的财富
一面明镜
照出了周遭的风景
一只天眼
看见了夜空的黎明
这真是一水成库百媚生
一站生电放光明哪
巴山水库成了“巴山湖”
标进了县里的旅游地图
画家过来支画板
摄影家过来对镜头
作家过来抒豪情
钓鱼竿伸来打比赛
摩托艇开来打比赛
旅游团这里那里的小红旗
在山光水色间争艳丽
有人评价眼前的风景说
就像画的一样美
有人评价画家的画说
就像真的一样美
这可把巴山人弄糊涂了
到底是画的比真的美
还是真的比画的美?
一条条公路过来了
一座座桥梁出现了
一道道隧洞贯穿了
沿湖的路 盘山的路
出县的路 出省的路
过河的桥 过街的桥
走人的桥 跑车的桥
过人的洞 过车的洞
过水的洞 过电的洞
远远近近里里外外的“电影气气”
弥漫在巴山的空气里
机械的气息 搏动的气息
新鲜的气息 希望的气息
给暮气沉沉的巴山带来几多惊喜
水库大梁上建起了机场
直升机趁着起落瞄一眼水库的秀色
高速路也在修建了
2022年要经过水库哩
渝西高铁列入了前期规划
也要和水库擦身而过
也要和冉家坝擦身而过
(当然也要和老房子擦身而过啰)
老房子却有些茕茕孓立
房拆了 人散了
只有居中的一栋立着
只有院坝的石榴树立着
四壁土墙 残檐乱瓦
一截躯干 临风瑟索
你是想做一个标本么
你是想存一段历史么
你是想留一点记忆么
你是想造一种反差么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陈氏家族长在这块屋基里
巴山农民生在这块土地上
这辈子我就活在这里了
这辈子我就定在这里了
走了还要回
走也走不远
这儿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
这儿如今是金山银山
这儿如今是大道通天
这儿如今是丰衣足食
这儿如今是幸福家园
云开了 天开了
山明了 水透了
满世界都敞敞亮亮的了
照见一个叫做“小康”的神灵
在秦巴山区的土地上
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
一亩三分 一亩三分 一亩三分……
无所不在地游荡
不留缝隙地游荡
决战决胜地游荡
全面凯歌地游荡
2020年1月初稿 2月修改
作者情况:向求纬, 男, 73岁,重庆市万州区人。196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大巴山区城口县待了20年(插队落户13年,工作7年),1985年调入万县日报(现三峡都市报)作主任编辑。已退休。
1966年开始在全国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以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见长,已写作、发表文学作品600多万字,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级获奖,作品曾被收入国内各种选集。曾主编10多套文学丛书,出版长篇叙事诗集《喊峡谣》、《老乡何其芳》,诗集《巴山情》、《三峡吟》、《三峡恋》、《搂定三峡》、《求纬朗诵诗》,散文集《远山的呼唤》、长篇散文集《巴山老知青》,报告文学集《大地不了情》、《三峡的脚步》、《永远的绿洲》,尤以2003年出版的以三峡移民为题材的长诗《喊峡谣》、2009年以何其芳为题材的长诗《老乡何其芳》和2014年出版的知青题材长篇散文《巴山老知青》较有影响。《巴山老知青》2017年获第七届重庆文学奖,已被改编为高清同名电影。现为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
通 讯 处:重庆市万州区三峡都市报社 邮 编:404000
电 话:(023)58139386(宅) 13668469726(手机)
邮 箱:395923883@qq.com
微 信:W13668469726
身份证号:512201194611030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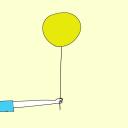


 (2次)
(2次)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