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发白的时候,就可以回家
我们站在草地上唱歌
天色就慢慢暗了下来
再暗一点,路就会发白
老人们说——
路发白的时候
就可以回家了
多年以后,在城里
我所能看到的路
都是黑色的
我所能遇到的夜
都是透亮的
而鬓角,却这么
轻易就白了
深处的记忆总会被酿成美酒
这首诗,创作于2015年秋天的一个凌晨。那时,我刚步入不惑之年。
我可能是诗人中最早接触互联网的那一批。
2004年开始,又在业余时间义务主编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从事藏族作家汉语作品的网络整理和代表作家研究工作。所以,更多时候,我都喜欢将自己的习作,第一时间发布到网络上,请诗友们批评。
记得这首诗刚写出来的时候,我就顺手贴到了微信朋友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我斗胆投给了《诗刊》,并发布在了中国诗歌网上。不曾想居然被中国诗歌网评为2016年1月14日“每日好诗”,《诗刊》2016年1月(上半月)也刊发了。
次年,又被中国诗歌网推荐到《诗刊》2017年12月(上半月)“E首诗”栏目再次发表。后来,这首诗先后被收录入《2016那中国诗歌年选》《诗歌点亮生活:中国诗歌网优秀作品选》《中国当代诗歌鉴赏》等多个选本。
诚如唐诗先生在“每日好诗”中的评语所言:“生活中处处充满诗意,只要您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诗神会随时光顾您。”这首诗的诞生,也真是这样一个自大而小、由深到浅、水到渠成的过程。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来自于生活的历练、沉淀和感悟。
这首诗也不例外,它是我近30年业余诗歌创作的凝结,也是扎根于故乡甘南的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打小熏陶浸染的结果。这让我愈发相信,深处的记忆,总会在某一时刻被酿成醉人的美酒!
这首诗的源起,也是奶奶小时候说过的一句话:“路发白的时候,就应该回家了。”
在那个远离现代化的时代,辛劳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劳作里,承接着自天而降的灵性,总结着口耳相传的智慧,留下了无数植根大地、言简意赅、寓意久远的谚语。
记忆的最深处,我的老祖母,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27岁的她就丧夫寡居。在那个贫寒艰苦的岁月里,以一名藏族女性的坚韧和宽厚,独自撑起了这个家,辛劳哺育了父辈兄妹3人和我们孙辈10余人,并且教导有方,各自成才。在老一辈人的口碑里,奶奶是集体吃大锅饭的困难时期全村子的“掌勺人”,也是村邻四舍调解家务最为信服的“大嫂”。
记忆的最深处,老木屋温暖的土炕上,慈祥的奶奶,用她在扫盲活动期间识得的不多几个汉字,指着墙上曾祖父题写的“朱子家训”条幅,教我和兄弟姐妹们仔细辨认着一个个日久发黄的汉字,给我和兄弟姐妹们淡淡地叙述着一辈子的辛劳和苦累,也让我们打小就耳闻目染着她朴素、温暖、干练、慈爱的高贵品格。
这一切,都让我想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名言:“伟大的女性,引导人类向上。”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在青青草地上放牧牛羊,是无比惬意而浪漫的事情。那也是所有在城市高耸的写字楼里奋力爬格子的人群,想象之外自由而散漫的天堂。
而唯有在夏日骄阳下真正放过牧的人,才会理解那种日复一日、无地自容的灼热和四顾无人、无可奈何的孤独。在怎么也等不到天黑的苍茫原野上,和牛羊絮叨、把会唱的歌谣一遍遍地唱完,就是放牧者打发时间的唯一乐趣。
“我们站在草地上唱歌/天色就慢慢暗了下来/再暗一点,路就会发白/”在钟表尚未普及的年代里,天色是唯一的报时器。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阡陌之间,用脚步反复踩出来的那一条条小道,是没有月色的暗夜里唯一闪亮的经纬,也是四野劳作的人们结束工作的信号,更是牧童们雀跃着奔向村庄的念想:“老人们说——路发白的时候/就可以回家了”。
这样的道路和方向,伴随着农家子弟的一生,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里,都烙下了痛楚而幸福的印记。纵使他们走出村寨再远,这条路的尽头,永远是那一盏油灯里反复闪耀着的乡村记忆。
“多年以后,在城里/我所能看到的路/都是黑色的/我所能遇到的夜/都是透亮的”。至今,走出村庄25年了,我依旧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人来人往的城市,街灯明亮的夜,那么多的璀璨,本来应该是彻底忘却村庄宁静而巨大暗夜的理由。可为何,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路口,在每一条宛若缎带的柏油马路上,我们踟躇的脚步,依旧会时时踩痛那些久远的记忆呢?!……
最无奈的是,我们尚未完全适应城市坚硬的道路,“而鬓角,却这么/轻易就白了”。——唐诗先生点评说:“这句诗行初读显得突兀,再读觉得自然,反复读觉得诗人在不露声色中将您的情绪彻底捕获了。”
而今,老祖母去世已经30余年了,先父也已归于黄土整整三载。作为长子,不惑之年,回家的这条路,即便是在白昼,都显得有点模糊了。而我是有多久,没有在故乡的暮色里,再去看一看那条夜路,是否依旧发白呢?
突然想起诗人阿信的话:“回得去的是老家,回不去的是故乡。”——我们走得并不太远。但是,我们还回得去吗?
也许,一首小诗,不应该承载这么多的情绪和记忆。博尔赫斯曾经说过,诗歌应该有的样子,乃是热情与喜悦。
2018年底,和我一起随赴海南采风的温州诗人瞿炜这样解读过我和我的诗歌:“对于他来说,表现于外的热情和喜悦,本质上是一种孤独和忧伤。这并不矛盾。所谓的热情和喜悦,来自他对诗歌的追求,而孤独和忧伤,是他来自人生的沉思和经验。他对故乡的眷恋,他的来自藏人的天性,都给了他一种谦卑的姿态,他乐于倾听,也乐于倾述,他毫无心机,但有辛辣的回应。”
我知道,在这个繁杂的世界上,自己拙于攻防,不擅博弈。那么,就继续保持一名诗歌爱好者的姿态,简单而安静地书写下去吧,在每一个晨曦破窗而来的黎明。
惟愿,在岁月温润之处,还能再次邂逅不期而遇的诗神!
我们站在草地上唱歌
天色就慢慢暗了下来
再暗一点,路就会发白
老人们说——
路发白的时候
就可以回家了
多年以后,在城里
我所能看到的路
都是黑色的
我所能遇到的夜
都是透亮的
而鬓角,却这么
轻易就白了
深处的记忆总会被酿成美酒
这首诗,创作于2015年秋天的一个凌晨。那时,我刚步入不惑之年。
我可能是诗人中最早接触互联网的那一批。
2004年开始,又在业余时间义务主编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从事藏族作家汉语作品的网络整理和代表作家研究工作。所以,更多时候,我都喜欢将自己的习作,第一时间发布到网络上,请诗友们批评。
记得这首诗刚写出来的时候,我就顺手贴到了微信朋友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我斗胆投给了《诗刊》,并发布在了中国诗歌网上。不曾想居然被中国诗歌网评为2016年1月14日“每日好诗”,《诗刊》2016年1月(上半月)也刊发了。
次年,又被中国诗歌网推荐到《诗刊》2017年12月(上半月)“E首诗”栏目再次发表。后来,这首诗先后被收录入《2016那中国诗歌年选》《诗歌点亮生活:中国诗歌网优秀作品选》《中国当代诗歌鉴赏》等多个选本。
诚如唐诗先生在“每日好诗”中的评语所言:“生活中处处充满诗意,只要您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诗神会随时光顾您。”这首诗的诞生,也真是这样一个自大而小、由深到浅、水到渠成的过程。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来自于生活的历练、沉淀和感悟。
这首诗也不例外,它是我近30年业余诗歌创作的凝结,也是扎根于故乡甘南的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打小熏陶浸染的结果。这让我愈发相信,深处的记忆,总会在某一时刻被酿成醉人的美酒!
这首诗的源起,也是奶奶小时候说过的一句话:“路发白的时候,就应该回家了。”
在那个远离现代化的时代,辛劳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劳作里,承接着自天而降的灵性,总结着口耳相传的智慧,留下了无数植根大地、言简意赅、寓意久远的谚语。
记忆的最深处,我的老祖母,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27岁的她就丧夫寡居。在那个贫寒艰苦的岁月里,以一名藏族女性的坚韧和宽厚,独自撑起了这个家,辛劳哺育了父辈兄妹3人和我们孙辈10余人,并且教导有方,各自成才。在老一辈人的口碑里,奶奶是集体吃大锅饭的困难时期全村子的“掌勺人”,也是村邻四舍调解家务最为信服的“大嫂”。
记忆的最深处,老木屋温暖的土炕上,慈祥的奶奶,用她在扫盲活动期间识得的不多几个汉字,指着墙上曾祖父题写的“朱子家训”条幅,教我和兄弟姐妹们仔细辨认着一个个日久发黄的汉字,给我和兄弟姐妹们淡淡地叙述着一辈子的辛劳和苦累,也让我们打小就耳闻目染着她朴素、温暖、干练、慈爱的高贵品格。
这一切,都让我想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名言:“伟大的女性,引导人类向上。”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在青青草地上放牧牛羊,是无比惬意而浪漫的事情。那也是所有在城市高耸的写字楼里奋力爬格子的人群,想象之外自由而散漫的天堂。
而唯有在夏日骄阳下真正放过牧的人,才会理解那种日复一日、无地自容的灼热和四顾无人、无可奈何的孤独。在怎么也等不到天黑的苍茫原野上,和牛羊絮叨、把会唱的歌谣一遍遍地唱完,就是放牧者打发时间的唯一乐趣。
“我们站在草地上唱歌/天色就慢慢暗了下来/再暗一点,路就会发白/”在钟表尚未普及的年代里,天色是唯一的报时器。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阡陌之间,用脚步反复踩出来的那一条条小道,是没有月色的暗夜里唯一闪亮的经纬,也是四野劳作的人们结束工作的信号,更是牧童们雀跃着奔向村庄的念想:“老人们说——路发白的时候/就可以回家了”。
这样的道路和方向,伴随着农家子弟的一生,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里,都烙下了痛楚而幸福的印记。纵使他们走出村寨再远,这条路的尽头,永远是那一盏油灯里反复闪耀着的乡村记忆。
“多年以后,在城里/我所能看到的路/都是黑色的/我所能遇到的夜/都是透亮的”。至今,走出村庄25年了,我依旧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人来人往的城市,街灯明亮的夜,那么多的璀璨,本来应该是彻底忘却村庄宁静而巨大暗夜的理由。可为何,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路口,在每一条宛若缎带的柏油马路上,我们踟躇的脚步,依旧会时时踩痛那些久远的记忆呢?!……
最无奈的是,我们尚未完全适应城市坚硬的道路,“而鬓角,却这么/轻易就白了”。——唐诗先生点评说:“这句诗行初读显得突兀,再读觉得自然,反复读觉得诗人在不露声色中将您的情绪彻底捕获了。”
而今,老祖母去世已经30余年了,先父也已归于黄土整整三载。作为长子,不惑之年,回家的这条路,即便是在白昼,都显得有点模糊了。而我是有多久,没有在故乡的暮色里,再去看一看那条夜路,是否依旧发白呢?
突然想起诗人阿信的话:“回得去的是老家,回不去的是故乡。”——我们走得并不太远。但是,我们还回得去吗?
也许,一首小诗,不应该承载这么多的情绪和记忆。博尔赫斯曾经说过,诗歌应该有的样子,乃是热情与喜悦。
2018年底,和我一起随赴海南采风的温州诗人瞿炜这样解读过我和我的诗歌:“对于他来说,表现于外的热情和喜悦,本质上是一种孤独和忧伤。这并不矛盾。所谓的热情和喜悦,来自他对诗歌的追求,而孤独和忧伤,是他来自人生的沉思和经验。他对故乡的眷恋,他的来自藏人的天性,都给了他一种谦卑的姿态,他乐于倾听,也乐于倾述,他毫无心机,但有辛辣的回应。”
我知道,在这个繁杂的世界上,自己拙于攻防,不擅博弈。那么,就继续保持一名诗歌爱好者的姿态,简单而安静地书写下去吧,在每一个晨曦破窗而来的黎明。
惟愿,在岁月温润之处,还能再次邂逅不期而遇的诗神!
注释:
原刊于“卓尔诗歌书店”微信公众号2019年5月3日“周末有约”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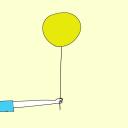


 (2次)
(2次)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