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在弥漫于诗坛和知识界的“现代主义热”渐渐消散之后,一位来自前东欧的真正的大师出现在中国诗人面前,他就是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米沃什1911年生于当时属波兰领土的立陶宛,二战时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曾参加抵抗运动,他所经历的一切,促使他以笔来叙述二十世纪人类的噩梦(我难以忘怀他那但丁式的笔触:“街上机关枪在扫射,子弹把路面的鹅卵石打得蹦了起来,就像豪猪身上长的箭刺”);战后,米沃什出任波兰驻美、法外交官,但他于1951年选择了自动离职,此后旅居巴黎,自1960年起定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文学,直到生命的晚年。米沃什的诗感情深沉、视野开阔,以质朴、诚恳的语言形式表达深邃复杂的经验,有一种历史见证人的沧桑感。1980年,这位被称为“另一个欧洲的代言人”,因为“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正因为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进入到中国诗人的视野。《世界文学》等杂志相继介绍了他的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外国诗》第5辑上刊载的他的一组诗(绿原译)和诗歌自传《诗的见证》(节选,马高明译),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位诗人的印象。但米沃什真正对中国诗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却是在1990年代以后。为什么呢?也许正是人们的时代经历使他们意识到这样一位诗人对他们的意义:
在恐惧和战栗中,我想我要实现我的生命
就必须让自己做一次公开的坦白,
暴露我和我的时代的虚伪…
这种看似直白的诗,却对那时的中国诗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力量。这使他们意识到那由时代和良知所赋予的艰难使命,也意识到他们自己要在写作中去努力“实现”的一切。的确,在1990年代初那些难忘的时日,重读《诗的见证》,它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对我产生了一种震动:
“我将本文命名为《诗的见证》,并非因为我们目睹诗歌,而是因为它目睹了我们。”
这就使我想起了杜甫的千古名句“国破山河在”。富有力量的正是一个“在”字——那养育了一代代生民的祖国山河正是一种“无言的存在”:不仅是我们在眺望它,也是它在“目睹”着我们。它无言地目睹着一切,并使一个诗人一夜间白了头。
我想,正是被置于这样的“目睹”之下,中国1990年代的诗歌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米沃什的这句话,经过传播,也直接变成了“不是我们目睹了诗歌,而是诗歌目睹了我们”,在诗人们中间流传开来。
这里,很难对米沃什做出全面的评述。实际上,这是一位深邃复杂、难以为我们所穷尽的作家。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和西川谈到米沃什时,西川甚至说在他那里体现了一种“邪恶的智慧”。这里,我只谈印象最深的几点,比如说米沃什诗中的那种沉痛感。他的那首以烧死布鲁诺为题材的名诗《鲜花广场》,就含有这种对历史的沉痛。米沃什是1943年在华沙写下这首诗的,他所经历的大屠杀和流放,他所目睹的对罪恶的欢呼或默许,使他看清了几百年前究竟是什么发生在罗马的那个广场上:那带着人类皮肉焦糊味的黑烟尚未消失,看客们“已回到他们的酒杯旁”,或是继续同集市上的小贩“讨价还价”!多年之后,纪念者也许会到来,但他们在这里读到的,不过是“在火堆熄灭前已诞生的遗忘”!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现出人类历史可怕的真相,更能刺伤一个人的良知呢?
也许,米沃什就是从这里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职责,那就是通过发出属于人类良知的声音,“保护我们免害于巨大的沉默”。
因此他不能安于那种先锋派的修辞游戏,也不能安于如他所说的“我们不曾以绝对的爱,超乎常人能力地,去爱萨克森豪森的可怜的灰烬”的“那种悔恨”。这使他选择了一条艰巨的、需要以火和剑来开辟的写作道路。
当然,米沃什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其道德勇气。记得前些年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着另一位东欧作家的一句话“活在真实中”。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谁能以“活在真实中”自诩?“活在真实中”,即意味着“活在压力下”,或者说“活在矛盾中”、“活在问题中”。
因而经常发生在米沃什诗中的那种自我拷问,对我来说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在一首题为《诱惑》的诗中,诗人写到他来到山坡上眺望星空下的他的城市,并带着他的“伙伴”——他那凄凉的灵魂。这首诗就这样带着一种自我对话和争辩的性质。诗中的诗句“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也深深地感动了我。是的,我最认同的就是这里的“试图”二字。面对一个时时超出了我们理解之外的世界,这种“试图”,是艺术的全部难度所在,但也是一个作家的勇气所在。是他的勇气所在,但也是他的全部诚实和智慧所在。
米沃什的诗,就这样带着历史赋予的重量和全部复杂性,呈现在中国1990年代诗人的面前。他的出现,使返回历史现场的中国诗人们对1980年代常谈及的“诗人何为”这一命题,有了一个坐标,也有了更切实的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理解。
当然,无论是米沃什,还是一个中国当代诗人,要面对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像米沃什这样的饱经沧桑的人,经历多了就会面对另一个比集中营更无形、也许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虚无”。在他的晚后期,他要应对的,就是这种已深入到时代骨髓中的虚无。一次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这样很沉痛地说:“我们这个世纪的诗人,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悲哀。每当我们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着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的一团,刻结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位诗人的意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在他的晚年,他以那种罕见的“帕斯卡尔式的热情”,更为深入地探讨着那些对人类存在更内在的问题。即使他写孤独,即使他做“寂寞研究”(这是他一首诗的题目),也闪耀着精神的元素,“使我们免于像银河一般的死寂”。我想,正是这种对人类(或者说对上帝)所怀有的责任,使米沃什的诗愈来愈开阔,也愈来愈有力量,成为一位非凡的二十世纪后半期硕果仅存的大师。
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劳作。
歌唱的鸟儿正落在忍冬花上。
在这世界上我不想占有任何东西。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不管我曾遭受过什么样的苦难,我都忘了。
想到我曾是那同样的人并不使我难受。
我身体上没感到疼。
挺起身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
(沈睿译)
这首诗颇受中国读者的喜爱。但它并不是一首一般的即景诗,对它的境界的体会,要结合到诗人的一生。正因此,这首诗才获得它的份量和意义。“挺起身来”的一瞬,漫长而充满苦难的历史被超越。而这超越的一刻,正是“神恩”所在,是“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瓦雷里《海滨墓园》)的时刻。这就是诗人要用“礼物”这个题目来命名这首诗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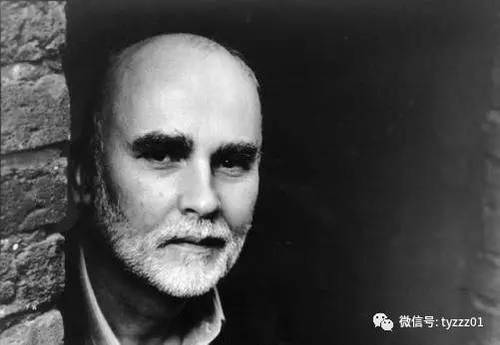
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
正因为米沃什,这里我想到了另一位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扎加耶夫斯基出身于利沃夫,二战后因该地划归苏联的乌克兰,随父母被遣返波兰。1972年出版诗集《公报》,成为“新浪潮”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81年当局发布戒严令后,被迫离开“营房般阴沉”的波兰,迁居法国。迄今,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享有广泛的声誉,被公认为是继米沃什、席姆博尔斯卡之后波兰最杰出的诗人。
第一次接触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是五六年前通过一位叫“桴夫”的译者。听带译稿来的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位原籍台湾、精通多种语言、业余时间一直爱好读诗、译诗的退休数学教授。他的这些译诗中,就有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集《神秘学入门》和米沃什编选的《世界诗选》。米沃什编选的这本诗选我早就听说过,并一直渴望读到,而“扎加耶夫斯基”这个陌生的名字则是第一次为我所知。
但是,一接触到他的诗,我就知道这是一位“精神同类”,我就有了深深的激动和认同。甚至,比起米沃什的诗,他的诗更使我感到亲切,也更能触动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难以言说的感受。在一首题为《自画像》的诗中他写到:“我看到音乐的三样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而这同样是构成这位东欧诗人作品感人力量的因素:
荷兰画家们
白鸈的钵,沉甸甸地流着金属感,
光照上圆鼓的窗。
铅色的云层厚得可以触到。
床单似的长袍,刚出水的牡蛎。
这些都会永垂不朽,却对我们无用。
木拖鞋自己在散步,
地板砖从不寂寞,
有时会和月亮下棋。
一个丑姑娘读着
无色墨水写成的信,
是诉爱还是讨钱?
桌布带着浆和道德的味道
表面和深度连不起。
神话?这儿没有神话,只有蓝天,
浮动,殷勤,像海鸥的唳鸣。
一个妇人安详地削着一只红苹果。
孩子们梦着老年。
有个人读着一本书(有一本书被读),
还有个人睡着了,一个温软的物体,
呼吸得像架手风琴。
他们喜欢流连,他们到处歇脚,
在木椅背上,
在乳色的小溪,狭如白令海峡,
门都开得宽敞,风很温和。
扫帚做完了工歇着。
家庭景象揭示一切,这里画的
是一个没有秘密警察的国家。
只有在年轻雷姆卜朗特的脸上
落下了早年的阴影,为什么?
荷兰画家们啊,告诉我们,什么
将发生,当苹果削完,当丝绸变旧,
当一切的颜色变冷,
告诉我们是黑暗。
(桴夫译)
这大概是诗人在欧洲某个艺术馆观看伦勃朗等著名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的作品后写下的一首诗。诗中,诗人对绘画艺术的独到感受已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了,然而他的思考和联想还不时地把我们引向历史和人生的更深广的层面。比如说,在描述了艺术的持久感人的生命力后,但又说它“对我们无用”,这就暗含着对当下一个实用主义时代的嘲讽。画中的桌布不仅带着浆过的味道,甚至也带着某种“道德的味道”,这也颇有意味。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句:“家庭景象揭示一切……”这一句来得突然,但又在骤然间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这不仅使我们把诗人所观看的西欧绘画与他所经历的“东欧经验”联系起来,而且使我们更深入地体会到诗人此时的内心颤栗。
诗的结尾也十分感人,当所有的观看最终触动了内心,诗人在最后发出了那样的询问。这不是一般的询问,而是更内在的迸发,是把这一切纳入到人类的普遍命运的高度来发问,因而如此震动人心。
的确,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西欧诗人会如此“观画”。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就这样带着他的祖国给他的全部赋予,带着他的悲剧和创伤,但也带着一个诗人的全部敏感和爱。因此,不难理解这样一位诗人为什么会很快引起中国诗人的注意。就在我读到桴夫的译作并把它推荐给一本杂志后不久,我又读到诗人黄灿然的译作和李以亮的译作。出于对扎加耶夫斯基等波兰诗人的珍爱,李以亮甚至自费排印了一本《波兰诗选》。他给我寄来了两本,另一本我送给了诗人多多。多多一接到它,眼睛一亮,马上就把它塞进了衣兜里,生怕被人发现似的!我想,这还是他在“文革”那个时代养成的习惯啊。
是的,这又是一场精神的“秘密接头”。我在以上引用的那句诗,其实全句应为:“我看到音乐的三种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种没有名字。”有了这“音乐的三种成分”已相当不错了,这说明肖邦的血液又秘密地流到了他的身上,而这个没有名字的第四种更耐人寻味,而它是什么?它也许就在下面这首题为《灵魂》的诗中:
我们知道,我们不被允许使用你的名字。
我们知道你不可言说,
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
疑心着神秘的伤害。
我们知道,现在你不被允许活在
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
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被告知——
你根本不在任何地方。
但是我们依然不断地听到你疲倦的声音
——在回声里,在抱怨里,在我们接到的
安提贡来自希腊沙漠的信件里。
(李以亮译)
灵魂存在吗?当然存在,就在这首诗里。虽然它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带着疲倦的声音,但它存在;虽然它不被允许活在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但它还是找到了一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这首诗,就是为灵魂辩护的一首诗。为诗一辩,也就是为灵魂一辩,这样才有更本质的意义。斯大林模式下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以铁腕否定灵魂的存在,西方工业技术文明、商业社会、大众文化时代、物质消费时代,同样漠然于灵魂的存在。扎加耶夫斯基一生经历了这两个时代,所以他要带着切身的痛感,起而为灵魂一辩。这就是我深深认同这位诗人的根本原因。
所以真正的诗歌不仅仅是审美,它更是一种进入灵魂的语言。海子在他的诗学绝笔《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于这种诗观。不过这种“烈火”很可能是一场“看不见的火”。像扎加耶夫斯基这样的诗人,终生便穿行在这看不见的、但一直在烧灼着他的火中。
当然,为灵魂一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地谈论灵魂。还是扎加耶夫斯基说得好“我看到音乐的三种成分……第四种没有名字”。我们只有保持敬畏,灵魂才有可能用它的沉默对我们讲话。
现在我们来看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首诗《飞蛾》,它选自米沃什编选的《世界诗选》。就是在这本诗选里,很多诗人我第一次知道,很多好诗我第一次读到。不过,许多诗读过之后也就记不起来了,但扎加耶夫斯基的这首《飞蛾》却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并让我不时地惊异于它的力量:
透过窗玻璃
飞蛾看着我们。坐在桌旁,
我们似被烤炙,以它们远比
残翅更硬,闪烁的眼光。
你们永远是在外边,
隔着玻璃板,而我们在屋内
愈陷愈深的内部,飞蛾透过
窗子看着我们,在八月。
(桴夫译)
人人都知道小飞虫的悲剧在于它的趋光性,我们在鲁迅的《秋夜》中也曾听到它“丁丁的乱撞”,一种声音的质感从深邃的秋夜里传来,一种小人物粉身碎骨扑向灯火的悲剧让我们心悸。但我们在凝视这样一种生命存在时,是否也感到了一种注视?
扎加耶夫斯基就感到了这种注视。正因为飞蛾的注视,并由此想到更广大的悲剧人生,诗人感到被“烤炙”,换言之,他的良心在承受一种拷打。愈陷愈深的内部,这是一种隐喻性的写法,但我们都知道诗人在说什么。
所以,诗中最后出现的不再是飞蛾,是“灵魂”出现了。不仅是我们在看飞蛾,也是某种痛苦的生灵在凝视我们——这首诗就这样写出了一种“被看”,一种内与外的互视。它让我们生活在一种米沃什所说的那种“目睹”之下。一个东欧诗人的“内向性”,就这样带着一种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内省的力量。
我们仍在接受着这种目睹。或者说,我们经历的全部生活会把我们带向这样一种“目睹”。写到这里,我又回到了几年前的初冬那个开始飘雪的下午,当我在昌平乡下公路上开车开到一辆卡车后面时,我不由得骤然降慢了车速,一首诗就在那样的时刻产生了: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
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诗写出后我一直被它笼罩着。“田园诗”这个诗题是诗写出来后加上去的,而这个诗题的出现似乎照亮了更深远的东西。我希望有心的读者能把该诗放在一个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读,以使它和“田园诗”这一古老的传统发生一种关联。如果这样来读,他们不仅会读出一种反讽意味,可能还会读出更多。
历史和文明一直在演变,羊依然是羊,它们一直用来作为“田园诗”的点缀,似乎没有它们就不成其为“田园诗”。甚至在一幅幅消费时代的房地产广告上,人们也没有忘记通过电脑合成在“乡村别墅”的周边点缀几只雪白的羊,以制造一种“田园诗意”的幻境。事实上呢,羊不过是在重复它们古老的悲惨命运。诗中写到它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依然怀着几分孩子似的好奇。它们的注视,撕开了我们良知的创伤。
我甚至想问,这种注视是谁为我们这些人类准备的?
诗的最后,是一双掩映在挡风玻璃后面的悲痛的眼睛。读者通过这双眼睛看到了什么呢?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在飞雪中消失、模糊的运羊车,还有我们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命运。在这种命运里,人与羊、大地上所有的生命已被纳入了某种相似的“程序”。
用一种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的方式来表述,在我写这首诗时,“奥斯维辛神话”就在我的心底无声地呐喊!
王家新,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等,另有诗论、编译多种。
本文来源:《天涯》2007年第6期。
{Content}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3次)
(3次) (12次)
(12次) (1次)
(1次) (4次)
(4次) (3次)
(3次) (2次)
(2次) (7次)
(7次) (2次)
(2次) (1次)
(1次) (1次)
(1次) (2次)
(2次) (1次)
(1次) (2次)
(2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3次)
(13次) (7次)
(7次) (1次)
(1次) (4次)
(4次) (2次)
(2次) (4次)
(4次) (1次)
(1次) (2次)
(2次) (3次)
(3次) (3次)
(3次)除每日好诗、每日精选、诗歌周刊等栏目推送作品根据特别约定外,本站会员主动发布和展示的“原创作品/文章”著作权归著作权人所有
如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用于他处和/或作为他用,著作权人及本站将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诗意春秋(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京ICP备19029304号-1 京ICP备16056634号-1 京ICP备16056634号-2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Copyright © 2006-2015 全景统计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