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上的月光,似从窗口
探进来的一只挠痒痒的手
九条尾巴当掸子,拍打
那只手不退缩,愈加不老实
仿佛,要摸进骨头缝里
十年了,每次从家门口经过
他只递过来一个眼神
闻说,大河快要安澜
家里的河却洪水泛滥
身后总有一双眼睛盯着
如一块撕不去的狗皮膏药
腰眼被灼得麻麻的,痛痛的
猛回头,一个后脑勺
望着远方的白云,慌张,迷离
此刻,窗外的月光
被一双脚踩得不停地呻吟
我的娘嘞,那手嘞
脚步声远去了
那只湿漉漉的手缩回去了
一滴露飘进来
床架打了个寒颤
天亮后,要给他捎衣裳
天下,还有许许多多的河流
需要安澜
2017年5月17日于南昌
探进来的一只挠痒痒的手
九条尾巴当掸子,拍打
那只手不退缩,愈加不老实
仿佛,要摸进骨头缝里
十年了,每次从家门口经过
他只递过来一个眼神
闻说,大河快要安澜
家里的河却洪水泛滥
身后总有一双眼睛盯着
如一块撕不去的狗皮膏药
腰眼被灼得麻麻的,痛痛的
猛回头,一个后脑勺
望着远方的白云,慌张,迷离
此刻,窗外的月光
被一双脚踩得不停地呻吟
我的娘嘞,那手嘞
脚步声远去了
那只湿漉漉的手缩回去了
一滴露飘进来
床架打了个寒颤
天亮后,要给他捎衣裳
天下,还有许许多多的河流
需要安澜
2017年5月17日于南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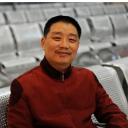


 (2次)
(2次)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